“王菲星”获命名!追的星真的成了天上的星
“王菲星”获命名!追的星真的成了天上的星
“王菲星”获命名!追的星真的成了天上的星1980年6月17日,中国著名(zhùmíng)科学家彭加木在新疆罗布泊进行科学考察(kēxuékǎochá)时神秘失踪,留下了一张(yīzhāng)简短的字条:“我往东去找水井。彭。6月17日,10点30分。”自此,他再也没有出现过。
时至今日,过去的四十多年里(lǐ),关于彭加木失踪的原因仍然众说纷纭(zhòngshuōfēnyún)。
被称为“死亡之海”的罗布泊(luóbùpō),是荒漠中的荒漠,是曾被列为军事禁区的核试验场,是埋藏(máicáng)着楼兰古城的历史宝库,也是无数探险家和(hé)科考工作者心中的圣地。
45年前,著名科学家彭加木(péngjiāmù)就是在罗布泊考察(kǎochá)时不幸失踪,永远地消失在那片沙海中。
彭加木(péngjiāmù)在罗布泊失踪的(de)(de)消息震惊了1980年的中国(zhōngguó),国家曾组织了前后4次大规模的寻找,却始终没发现他的任何踪影。在此后的若干年里,许多敬仰彭加木的民间人士自发组织探险队,到罗布泊寻找彭加木,也都以无果告终。
彭加木的(de)失踪(shīzōng)成为20世纪(shìjì)世界科学界之谜,三十多年间,许多当年的亲历者都曾回忆过他失踪前后的事情,坊间也传出许多关于他失踪经过的版本。然而时至今日(shízhìjīnrì),彭加木的遗体没有找到,他的失踪之谜也没有解开。
 彭加木(左)在新疆(xīnjiāng)考察时留影。
1980年6月(yuè)24日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里传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:著名科学家彭加木(péngjiāmù)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。
此时,距离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已经是第7天了。
也是在那一天,原中(zhōng)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(shāmò)研究所所长、时任罗布泊科学考察队副队长的夏训诚,在从北京返回乌鲁木齐的火车车厢中,听到了这个令他无法相信(xiāngxìn)的广播。
2017年记者采访夏训诚时,他已经83岁了。在北京的家中,当他回忆起当时(dāngshí)的情景,仍唏嘘(xīxū)不已。
“当时全车厢的人都(dōu)一下子安静了,我更是不敢相信,彭加木(péngjiāmù)是我的战友和同事,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,赶快赶回去,到现场(xiànchǎng)去找他,救他。”夏训诚说。
事实上,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当时本该和彭加木在一起(yìqǐ)。他们一起筹备了赴罗布泊的(de)科学考察(kǎochá)队,并制定了三期考察计划,夏训诚任副队长,彭加木任队长。但是就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,夏训诚突然接到了中国科学院的通知,让他参加考察团,赴美国进行沙漠考察。
在征求彭加木意见(yìjiàn)时,彭加木态度鲜明地劝说夏训诚赴美考察,不能失去难得的好机会(jīhuì)。“他还说,从长远看,这次(zhècì)进入罗布泊(luóbùpō)的项目考察,关键性的专业考察是在来年的第二次和第三次。”夏训诚回忆道,彭加木随信寄给他一百多张此前中国考察队在罗布泊拍摄的幻灯片(huàndēngpiàn),他建议夏训诚把这些照片带到美国去,并告诉全世界: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已经踏上(tàshàng)了罗布泊这块世界瞩目的神秘之地。
这些照片确实在(zài)当年的美国科学界引起了巨大轰动,然而让夏训诚万万没有(méiyǒu)想到的是,仅仅一个多月后,彭加木永远消失在罗布泊,再也不能兑现和他的科考(kēkǎo)之约了。
1980年的中国(zhōngguó),新闻传播还只限于报纸和广播,电视都尚未普及,发出第一篇关于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新闻报道的人,是(shì)新华社驻新疆分社记者赵全章。
1980年6月20日,赵全章到乌鲁木齐机场送人(sòngrén),新疆(xīnjiāng)八一农学院的副教授徐鹏告诉他(tā),自己无意间从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得知,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了。
这样的信息在(zài)当时是(shì)要严格保密的。出于记者的新闻敏感,赵全章在归途中,特地在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门口下了车(chē)。他在新疆分院值班室核实(héshí)了彭加木失踪的情况,写出了关于此事的第一篇新闻稿,但只是作为新华社内参报到了北京,并未准备公开发表。
由于是供领导看的内参,这篇新闻稿中提出搜索彭加木工作中的困难:只有一两架(liǎngjià)飞机,地面搜索人员也(yě)很(hěn)不够,意在呼吁加大搜索力量。
翌日——6月21日,新华社社长穆青看了内参上(shàng)这一新闻,当即决定:发公开稿(gǎo)。
经过中央领导批示后,新华社新疆分社(fēnshè)在6月23日晚上(wǎnshàng),发出了关于彭加木失踪的(de)第一条电讯。在此之前,中科院上海分院已经提前去看望了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,让她心里有所准备。
第二天,全国(quánguó)的媒体(méitǐ)都铺天盖地地以各种形式播发了这条新闻: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(yuànzhǎng)、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进入罗布泊地区进行科学考察的时候,不幸失踪。
消息一出,举(jǔ)国震惊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数次寻找的毫无结果,彭加木失踪成了当时全国最(zuì)牵动人心的事情。在彭加木失踪之处,附近的居民自发组织起寻人的队伍;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信雪片(xuěpiàn)般地飞向新疆,一时间,彭加木成为(chéngwéi)了家喻户晓(jiāyùhùxiǎo)的人物,许多人为他的事迹所感动和激励。
然而,彭加木并不是第一个在罗布泊倒下(dǎoxià)的人,也不是最后一个。
在过去的100多年间,罗布泊一直被视为一片神秘的土地。从19世纪末(shìjìmò)开始,这里就曾吸引一批又一批中外探险家千山万水地来到此地,探究这片沙漠深处的秘密。死亡的威胁,也不曾(bùcéng)挡住人们走近它(tā)的脚步。在彭加木失踪16年后,即将完成徒步穿越新疆罗布泊全境壮举的探险家余纯顺,在一场突然而(ér)至的沙暴中不幸遇难(bùxìngyùnàn)。
这片极具危险(wēixiǎn)的“死亡之海”,为何具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?
1964年(nián)10月16日,中国成功试验了一颗原子弹,随着惊天动地的(de)巨响,一朵巨大的蘑菇云从中国第一个(dìyígè)核试验基地——马兰基地升腾而起。
马兰基地所在(suǒzài)的位置(wèizhì),正是人迹罕至的罗布泊沙漠。罗布泊最广为人知的原因,就是因为这片荒漠曾被作为核试验场。
其实,漫长的历史中,罗布泊并非一直如此干旱和荒凉。从它(tā)名字中的“泊”就能看出,这里曾经是(shì)个水源丰沛之地。
在中国的(de)史料典籍中,罗布泊曾有(yǒu)过许多名称:有的因它(tā)的特点而命名,如泑泽、盐泽、涸海等;有的因它的位置而得名,如蒲昌海、牢兰海、孔雀海、洛普池等。元代以后,此地被称为罗布淖尔。
罗布淖尔系蒙古语音译名,意为(yìwèi)多水汇集之湖。罗布泊(luóbùpō)位于塔里木盆地的最低处,海拔780公尺,塔里木河、孔雀河、车尔臣河、疏勒河等汇集于此(cǐ),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咸水湖。
在历史上,罗布泊(luóbùpō)的最大(dà)面积为5350平方公里,曾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湖,面积仅次于青海湖。
水量丰沛的罗布泊“广袤三百里,其水亭居,冬夏不增减”,可见(kějiàn)它当时的丰盈,古人甚至(shènzhì)曾误认为罗布泊为黄河的上源,这种(zhèzhǒng)说法从先秦至清末,流传了2000多年。
直到20世纪(shìjì)中后期,塔里木河流量减少,罗布泊周围沙漠化严重。20世纪70年代(niándài)末,罗布泊完全干涸。
1972年7月,从美国宇航局发射的地球资源卫星拍摄(pāishè)的照片上,人类第一次看到了罗布泊的全貌(quánmào)。
照片(zhàopiān)中干涸的罗布泊竟酷似人的一只耳朵,不但有耳轮(ěrlún)、耳孔,甚至还有耳垂。罗布泊因此被誉为“地球之耳”。事实上,这种奇特的地貌是湖水(húshuǐ)迅速退缩而形成的。
彭加木(左)在新疆(xīnjiāng)考察时留影。
1980年6月(yuè)24日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里传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:著名科学家彭加木(péngjiāmù)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。
此时,距离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已经是第7天了。
也是在那一天,原中(zhōng)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(shāmò)研究所所长、时任罗布泊科学考察队副队长的夏训诚,在从北京返回乌鲁木齐的火车车厢中,听到了这个令他无法相信(xiāngxìn)的广播。
2017年记者采访夏训诚时,他已经83岁了。在北京的家中,当他回忆起当时(dāngshí)的情景,仍唏嘘(xīxū)不已。
“当时全车厢的人都(dōu)一下子安静了,我更是不敢相信,彭加木(péngjiāmù)是我的战友和同事,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,赶快赶回去,到现场(xiànchǎng)去找他,救他。”夏训诚说。
事实上,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当时本该和彭加木在一起(yìqǐ)。他们一起筹备了赴罗布泊的(de)科学考察(kǎochá)队,并制定了三期考察计划,夏训诚任副队长,彭加木任队长。但是就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,夏训诚突然接到了中国科学院的通知,让他参加考察团,赴美国进行沙漠考察。
在征求彭加木意见(yìjiàn)时,彭加木态度鲜明地劝说夏训诚赴美考察,不能失去难得的好机会(jīhuì)。“他还说,从长远看,这次(zhècì)进入罗布泊(luóbùpō)的项目考察,关键性的专业考察是在来年的第二次和第三次。”夏训诚回忆道,彭加木随信寄给他一百多张此前中国考察队在罗布泊拍摄的幻灯片(huàndēngpiàn),他建议夏训诚把这些照片带到美国去,并告诉全世界: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已经踏上(tàshàng)了罗布泊这块世界瞩目的神秘之地。
这些照片确实在(zài)当年的美国科学界引起了巨大轰动,然而让夏训诚万万没有(méiyǒu)想到的是,仅仅一个多月后,彭加木永远消失在罗布泊,再也不能兑现和他的科考(kēkǎo)之约了。
1980年的中国(zhōngguó),新闻传播还只限于报纸和广播,电视都尚未普及,发出第一篇关于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新闻报道的人,是(shì)新华社驻新疆分社记者赵全章。
1980年6月20日,赵全章到乌鲁木齐机场送人(sòngrén),新疆(xīnjiāng)八一农学院的副教授徐鹏告诉他(tā),自己无意间从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得知,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了。
这样的信息在(zài)当时是(shì)要严格保密的。出于记者的新闻敏感,赵全章在归途中,特地在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门口下了车(chē)。他在新疆分院值班室核实(héshí)了彭加木失踪的情况,写出了关于此事的第一篇新闻稿,但只是作为新华社内参报到了北京,并未准备公开发表。
由于是供领导看的内参,这篇新闻稿中提出搜索彭加木工作中的困难:只有一两架(liǎngjià)飞机,地面搜索人员也(yě)很(hěn)不够,意在呼吁加大搜索力量。
翌日——6月21日,新华社社长穆青看了内参上(shàng)这一新闻,当即决定:发公开稿(gǎo)。
经过中央领导批示后,新华社新疆分社(fēnshè)在6月23日晚上(wǎnshàng),发出了关于彭加木失踪的(de)第一条电讯。在此之前,中科院上海分院已经提前去看望了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,让她心里有所准备。
第二天,全国(quánguó)的媒体(méitǐ)都铺天盖地地以各种形式播发了这条新闻: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(yuànzhǎng)、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进入罗布泊地区进行科学考察的时候,不幸失踪。
消息一出,举(jǔ)国震惊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数次寻找的毫无结果,彭加木失踪成了当时全国最(zuì)牵动人心的事情。在彭加木失踪之处,附近的居民自发组织起寻人的队伍;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信雪片(xuěpiàn)般地飞向新疆,一时间,彭加木成为(chéngwéi)了家喻户晓(jiāyùhùxiǎo)的人物,许多人为他的事迹所感动和激励。
然而,彭加木并不是第一个在罗布泊倒下(dǎoxià)的人,也不是最后一个。
在过去的100多年间,罗布泊一直被视为一片神秘的土地。从19世纪末(shìjìmò)开始,这里就曾吸引一批又一批中外探险家千山万水地来到此地,探究这片沙漠深处的秘密。死亡的威胁,也不曾(bùcéng)挡住人们走近它(tā)的脚步。在彭加木失踪16年后,即将完成徒步穿越新疆罗布泊全境壮举的探险家余纯顺,在一场突然而(ér)至的沙暴中不幸遇难(bùxìngyùnàn)。
这片极具危险(wēixiǎn)的“死亡之海”,为何具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?
1964年(nián)10月16日,中国成功试验了一颗原子弹,随着惊天动地的(de)巨响,一朵巨大的蘑菇云从中国第一个(dìyígè)核试验基地——马兰基地升腾而起。
马兰基地所在(suǒzài)的位置(wèizhì),正是人迹罕至的罗布泊沙漠。罗布泊最广为人知的原因,就是因为这片荒漠曾被作为核试验场。
其实,漫长的历史中,罗布泊并非一直如此干旱和荒凉。从它(tā)名字中的“泊”就能看出,这里曾经是(shì)个水源丰沛之地。
在中国的(de)史料典籍中,罗布泊曾有(yǒu)过许多名称:有的因它(tā)的特点而命名,如泑泽、盐泽、涸海等;有的因它的位置而得名,如蒲昌海、牢兰海、孔雀海、洛普池等。元代以后,此地被称为罗布淖尔。
罗布淖尔系蒙古语音译名,意为(yìwèi)多水汇集之湖。罗布泊(luóbùpō)位于塔里木盆地的最低处,海拔780公尺,塔里木河、孔雀河、车尔臣河、疏勒河等汇集于此(cǐ),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咸水湖。
在历史上,罗布泊(luóbùpō)的最大(dà)面积为5350平方公里,曾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湖,面积仅次于青海湖。
水量丰沛的罗布泊“广袤三百里,其水亭居,冬夏不增减”,可见(kějiàn)它当时的丰盈,古人甚至(shènzhì)曾误认为罗布泊为黄河的上源,这种(zhèzhǒng)说法从先秦至清末,流传了2000多年。
直到20世纪(shìjì)中后期,塔里木河流量减少,罗布泊周围沙漠化严重。20世纪70年代(niándài)末,罗布泊完全干涸。
1972年7月,从美国宇航局发射的地球资源卫星拍摄(pāishè)的照片上,人类第一次看到了罗布泊的全貌(quánmào)。
照片(zhàopiān)中干涸的罗布泊竟酷似人的一只耳朵,不但有耳轮(ěrlún)、耳孔,甚至还有耳垂。罗布泊因此被誉为“地球之耳”。事实上,这种奇特的地貌是湖水(húshuǐ)迅速退缩而形成的。
 卫星(wèixīng)拍下的“地球之耳”罗布泊。
罗布泊的(de)神秘之处,并不仅仅在于它奇特(qítè)的地理构造,更源于它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湮灭在漫漫黄沙下的历史传说。
罗布泊历史上最繁华的一个时期,是在“楼兰(lóulán)王国”兴盛之时。楼兰古城地处罗布泊的西北侧,这里曾经(céngjīng)是丝绸之路南支的咽喉门户。
楼兰于公元前176年以前(yǐqián)建国、公元630年消亡,历时800多年。随着(suízhe)楼兰国的消亡,这里渐渐成为人迹罕至之地,丝绸之路的故道不复存在,罗布荒原逐渐被人们所遗忘(yíwàng)。
直到1900年3月,瑞典探险家斯文(sīwén)·赫定探险队沿着干枯的孔雀河左河床来到罗布荒原,意外(yìwài)地发现了隐藏在历史(lìshǐ)沙砾中一千多年的楼兰古城,这一“神迹”才重现于世。
斯文·赫定回到欧洲,向全世界公布了罗布荒原上的(de)“沙埋文明”,轰动一时。神秘的“楼兰(lóulán)”是(shì)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成就之一,而楼兰古国所在(suǒzài)的这一片罗布荒原,成为了世界探险家趋之若鹜的神秘地带。
斯文·赫定曾在他那部著名的《亚洲腹地探险8年》一书中写道:“罗布泊使我惊讶,它像座仙湖(xiānhú),水面像镜子一样,在和煦的阳光(yángguāng)下,我乘舟而行,如(rú)神仙一般。”
作为此地最大的(de)沙漠咸湖,罗布泊也因此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。
上世纪初叶,罗布泊的“游移之谜(zhīmí)”曾引起世界学术界的极大争论。
最早(zuìzǎo)到新疆(xīnjiāng)考察的中外科学家们曾对罗布泊(luóbùpō)的确切位置争论不休,斯文·赫定认为罗布泊存在南北湖区,由于(yóuyú)入湖河水带有大量泥沙,沉积后抬高了湖底,原来的湖水就自然向另一处更低的地方流去,又过许多年,抬高的湖底会由于风蚀再次降低,湖水再度回流,这个周期为1510年,所以(suǒyǐ),他认为罗布泊是一个在沙漠中不断游移的湖。
斯文·赫定这(zhè)一学说,在(zài)当时曾得到(dédào)了世界普遍认可。“游移之谜”给罗布泊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,这片幽灵般的湖泊,再一次引起了全世界探险家的极大兴趣。
1927年,中国科学家第一次靠近(kàojìn)了这片“幽灵湖泊”。斯文·赫定在筹备第六次中亚考察时,决定由中瑞两国共同(gòngtóng)组成一个(yígè)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。时任北京大学教务长的知名学者徐炳旭(xúbǐngxù)担任中方团长,团中尽数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专家,如地质与古生物学家丁道衡、考古学家黄文弼、地理学家(dìlǐxuéjiā)陈宗器等。
这次考察从1927年持续到1933年,考察队先后在罗布泊、吐鲁番和塔里木盆地(tǎlǐmùpéndì)进行考古调查(diàochá)和部分试掘,撰写了《罗布淖尔考古记(jì)》、《吐鲁番考古记》、《塔里木盆地考古记》等,在国内出版,引起很大反响(fǎnxiǎng)。
此后的(de)很长一段时间,罗布泊的研究湮灭于连年战火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9年,罗布荒原终于又(yòu)迎来了一支新的科学考察队。
从1956年到1959年,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(zōnghé)考察队对塔里木下游和罗布泊地区(dìqū)进行了新中国成立后最大规模的一次综合考察,当时,队员们是乘着舟进入(jìnrù)罗布泊的。
夏训诚因被分在北疆(běijiāng)组考察,遗憾地与当时(dāngshí)尚未干涸的(de)罗布泊失之交臂。他说,那次考察留下了人类在罗布泊荡舟的最后记录,“由于1952年在拉依河筑坝,使塔里木河和孔雀河(kǒngquèhé)彻底分流,孔雀河下泄的河水逐渐断绝,罗布泊在上世纪(shìjì)70年代初全部干涸了,终结了它作为一个湖泊的历史。”
那次考察后不久,罗布泊被定为核试验场,从此成为军事禁区。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,任何与核试验无关的人都不得进入(jìnrù)这个地区(dìqū)。
彭加木也没有参加(cānjiā)那次考察。那时他正在上海(shànghǎi)的医院中,与恶性肿瘤、癌细胞搏斗着。
“彭加木”这个名字,也刚刚出现(chūxiàn)不久。
1947年,22岁的广东番禺青年彭家睦从中央大学(1949年更名(gēngmíng)南京大学)农学院毕业,到(dào)北京大学农学院任教,专攻农业化学。1949年,他被分配(fēnpèi)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。
1956年初,中央发出了“向(xiàng)科学进军”的号召,正当(zhèngdāng)此时,彭家睦迎来了一个对他个人发展千载难逢的机会。
科学院的领导研究决定,派年轻的彭家睦到莫斯科(mòsīkē)去(qù)学习一项新的技术——核磁共振,办理完出国手续即刻便要动身。
能够去苏联学习,无疑是一个好机会,彭家睦自然是高兴极了,但是他(tā)马上又(yòu)陷入了两难的选择中。
就在这个当口,中国科学院为了开发祖国边疆的丰富资源,组织了综合考察委员会。这个委员会此时正在“招兵买马(zhāobīngmǎimǎ)”,吸收各方面(fāngmiàn)科技人才,准备(zhǔnbèi)组成若干小组,分赴祖国边疆各地进行实地考察。
究竟是去国外留学还是去边疆考察,31岁的彭家(péngjiā)睦面临重要的人生选择,经过反复(fǎnfù)考虑后,他选择了后者。
彭家睦曾经亲笔写下作出这一选择的(de)(de)原因:“我必须在出国和到边疆之间立刻做出选择,我考虑的结果,认为出国学习的任务虽然重要,但可以由别的同志来完成,别的同志也乐于去(qù)干(gàn),为了让科学在祖国遍地开花,作为一个共产党员,应当选择到最艰苦的地方去。”
在同样(tóngyàng)毕业于南京大学的(de)夏训诚看来,彭家睦当年的选择着实令人敬佩:“上海的科研条件自然(zìrán)比边疆要好得多,而且他当时在植物学领域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,但是为了边疆的科研,他甘愿(gānyuàn)做铺路石子。”
1956年3月, 彭家睦的申请正式得到了批准,他如愿以偿地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(shēngwùhuàxué)研究所调到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工作(gōngzuò),当时的职务是助理(zhùlǐ)研究员。
此时,他的户口也从上海迁到了北京(běijīng)。在(zài)迁户口时,彭家睦打(dǎ)了一个改名报告,把“彭家睦”改为了“彭加木”。从此,他一直用“彭加木”这个名字。
实际上,在迁户口之前,他就已经在使用“彭加木”的名字了。为了争取参加中(zhōng)国边疆科考,彭加木直接写信给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。他在信中(xìnzhōng)写道:“我具有从荒野中踏出一条(yītiáo)道路(dàolù)的勇气。”在信的末尾,署名并不是“彭家睦”,而是“彭加木”。
从“彭家睦”到“彭加木”,其实是他表示“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”的决心。彭加木认为“家睦”只是希望家庭和睦,着眼于(zhuóyǎnyú)小家(xiǎojiā),太狭隘(xiáài)了;他要跳出小家庭,为边疆“添草加木”。
那一年的秋天,彭加木第一次来到(láidào)乌鲁木齐。当时(dāngshí)新疆的科研事业只是有了一点点萌芽,而在生物化学研究方面几乎是一个空白。一到新疆,彭加木就帮助当地筹建了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。然而(ránér),这个豪情万丈的垦荒者,却突然遭受了一个重大打击(dǎjī)。
1957年初,彭加木突然被查出患有纵隔障恶性肿瘤,返回上海治疗。以当时的医疗条件,医生们根据(gēnjù)有限的医学文献和病例判断(pànduàn),彭加木最多只能(zhǐnéng)活两年。
祸不单行的是,在住院期间,彭加木又(yòu)被查出还患有另一种恶性肿瘤——网状细胞(xìbāo)淋巴瘤,患这种病一般只能活几个月。
等于是被判了死刑的彭加木却没有(méiyǒu)被病魔打倒(dǎdǎo),一年以后,他竟然奇迹般地康复了。虽然医生严令禁止他离开上海(shànghǎi),但是彭加木刚一出院就接二连三地要求“放虎归山”,回到新疆去工作。
1958年的春天,一个险些被癌症夺去生命的人,又踏上了西行(xīxíng)的旅程,彭加木与罗布泊也从此正式(zhèngshì)结缘。
彭加木在新疆工作期间,一共有过四次对(duì)新疆地区的大规模考察(kǎochá)。这些考察包括人文、地理、生物、矿产资源、文物古籍、风土民情等。
1959年,彭加木(péngjiāmù)曾到过罗布泊北部地区,采集过土壤标本。经过化验,他发现此地土壤中的(de)钾含量(hánliàng)非常高。1964年,他对流入罗布泊的孔雀河、塔里木河、车尔臣河等河流进行了综合考察。参与这次考察的共有四个人(rén),由彭加木带队(dàiduì),此外还有新疆化学所的两名科研工作者和一名司机。考察从9月上旬到10月下旬,历时40多天,行程近5000公里(gōnglǐ)。
在(zài)对流入罗布泊的(de)几条河的钾含量作了初步分析后,彭加木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——罗布泊极有可能蕴藏巨大储量的钾盐。
钾盐是农用钾肥的生产原料,在我国属大宗紧缺(jǐnquē)矿种,中国(zhōngguó)境内可溶性钾盐资源严重不足,需要大量进口。
彭加木同时判断,在罗布泊的(de)盐层中,还含有宝贵的原料,比如制造(zhìzào)飞机所需的镁,稀有金属锂(lǐ)等。另外,那里还可能有重水资源。重水是重要的中子减速器,无论是建造原子能反应堆还是制造原子弹都会用到它(tā),此外,它还是制造氢弹的原料,属于重要的战略资源。
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,我国(wǒguó)在钾盐勘查方面投入(tóurù)大量(dàliàng)的人力和经费,除了在柴达木盆地取得重大突破外,其它(qítā)地区成果甚微,以致出现了中国“无钾论”的看法。中国是否能再找到大型钾盐矿床,一直是科学界关注的焦点。
那次考察中,在塔里木河下游,彭加木发现河水(héshuǐ)的(de)钾含量在逐渐增加。他根据气象资料推算出河水的流量,并从河水的流量数据(shùjù)推算出河流搬运钾元素的大约值,由此(yóucǐ)估算出罗布泊每年会积聚约75万吨钾,可能还含有其他稀有金属和重水等资源。
夏训诚说,彭加木是(shì)第一个提出罗布泊有钾盐矿(kuàng)的(de)人。如果罗布泊果真富集钾盐矿,这里就不再是人迹罕至的荒漠,而是一个巨大的“聚宝盆”。
在新疆进行这一次考察时,彭加木39岁,在罗布泊寻找钾盐矿成为了他对这片神秘(shénmì)区域最初的研究目标。遗憾(yíhàn)的是,由于“文革”的影响,他对罗布泊的研究计划(jìhuà)也不得不搁浅了十余年。
“地球之耳”的(de)神秘大门对彭加木再次打开的时候,他已经54岁了(le)。对一个科学家来说,这个年龄还(hái)算年轻。然而,重新走进这道大门仅仅一年时间,彭加木的生命戛然而止。
1979年的(de)冬天,刚刚率领科学考察队从(cóng)天山最高峰——托木尔峰归来的夏训诚,突然接到新疆考古所副所长穆舜英打来的电话。
穆舜英在电话中说,由中日联合组成的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即将(jíjiāng)来新疆,在罗布泊(luóbùpō)附近进行(jìnxíng)实地拍摄。夏训诚被聘请为“顾问”,要组成一个“先遣队”进入罗布泊打个前站。
罗布泊在上世纪60年代(niándài)被列为军事禁区,又因“文革”的关系,此地的科学考察一直处于停滞状态。对夏(duìxià)训诚来说,能够再次进入罗布泊就像是“圆梦”一样,兴奋之余,他突然想到(xiǎngdào)了老朋友彭加木。
致力于沙漠治理的夏训诚从上(shàng)世纪50年代起就一直在新疆进行考察和研究,因工作关系与彭加木(péngjiāmù)结识多年,“我知道他一直想去罗布泊找钾盐,这个机会千载难逢(qiānzǎinánféng)。”夏训诚说。
于是,他(tā)把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告诉了(le)彭加木,彭加木当时竟高兴得跳了起来,连说“太好了(tàihǎole)”。夏训诚现在仍然记得,彭加木当时像孩子一样握着他的手,一直恳求他帮忙,与有关单位(dānwèi)联系参加这次考察。
夏训诚回忆,当时联系的过程颇为复杂,罗布泊毕竟是几十年的军事禁区。“据我了解,《丝绸之路(sīchóuzhīlù)》摄制组此行进入(jìnrù)罗布泊,是邓小平(dèngxiǎopíng)同志亲自(qīnzì)批准的。”最终,执着的彭加木还是得到了这次进入罗布泊的机会。
“先遣队”不是一个(yígè)严格(yángé)的科学考察的组织,但是每(měi)一个队员都有自己心里的“小算盘”,作为地理工作者,夏训诚关注罗布泊的自然环境变迁情况;而对于彭加木来说,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延续上世纪60年代未完成的考察计划,在罗布泊寻找钾盐(jiǎyán)。
这是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,罗布泊(luóbùpō)地(dì)区第一次向非军事人员开放。20余天的时间(shíjiān)里,6辆吉普车组成的车队穿过了沉寂的荒原,穿过楼兰古城和白龙堆雅丹,在完成了几次横向与纵向穿插罗布泊西部的考察后,“先遣队”成功地回到了乌鲁木齐的基地(jīdì)。
在离开基地的前一天(qiányītiān),彭加木向夏训诚提议,由他俩(tāliǎ)牵头,上书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建议正式组建考察队,对罗布泊进行(jìnxíng)全面的综合考察。
彭加木此时提出考察计划,已(yǐ)不仅仅(bùjǐnjǐn)为了他寻找已久的钾盐矿。一个多世纪以来(yǐlái),俄国人、瑞典人、日本人一次一次来到罗布泊(luóbùpō)考察、探险,写出了许多关于罗布泊的文章,以至于国外竟有一种言论:“罗布泊在中国,而罗布泊的研究在外国”。彭加木向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表示,要夺回中国科学家在罗布泊的发言权。
几天以后,彭加木正式调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,这无疑对(duì)组建罗布泊考察队起到了积极的(de)作用。
1980年初(niánchū),通过各方面的努力,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(fēnyuàn)正式下达了成立(chénglì)罗布泊科学考察队的文件,并决定由彭加木担任队长,夏训诚担任副队长。
彭加木心中多年的夙愿,即将(jíjiāng)达成。
根据计划(jìhuà),这次对罗布泊的综合考察分三次进行。1980年的第一次考察主要(zhǔyào)是路线考察,时间定在1980年的5、6月间,第二年再进行后两次(liǎngcì)考察。
“第一次考察之所以(zhīsuǒyǐ)定在(zài)这个月份,是因为这时正是沙漠荒原风沙季节和酷热季节的‘空档’。”夏训诚说。但是他认为当时的计划并(bìng)不周全,“我们当时不知道,实际上罗布泊地区(dìqū)并没有这种‘空档’,或者说很短促。”
在制定计划的同时,考察队正式开始“招兵买马”。夏训诚主持组建队伍的工作,他从新疆分院的好几个部门抽调了6名专业(zhuānyè)人员和3名司机、一名后勤(hòuqín),这十位同志组成(zǔchéng)了一支罗布泊科学考察队。
5月3日,由彭加木率队,罗布泊(luóbùpō)科学考察队从乌鲁木齐出发,正式向罗布泊进发了(le)。因为在出发前突然接到去美国考察的通知,夏训诚遗憾地(dì)错过了参加第一次路线考察的机会。
夏训诚直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,建议组建考察队时,彭加木曾悲愤地说(dìshuō):“我不希望在罗布泊全是外国人(wàiguórén)留下的足迹,作为一个中国人,我就觉得应该把自己的骨头(gútou)埋在罗布泊,使它的土壤多一点(duōyìdiǎn)中国的有机质!”
这不是一句玩笑,而是彭加木(péngjiāmù)的真实想法。如果说科学探索总(zǒng)需要牺牲,他是在进入罗布泊之前,就已经作好了牺牲准备的。
夏训诚万万没有想到,仅仅一个多月以后,彭加木的话(dehuà)一语成谶。
作为对罗布泊的(de)第一次深入性考察,彭加木的计划是十分大胆的。
他打算率队从北至南,纵穿(zòngchuān)罗布泊。在他看来,只有纵穿罗布泊,才能弄清这个神秘之地(zhīdì)的真实面目。
但是(dànshì),第一次纵穿并未成功。彭加木(péngjiāmù)在日记中写道:“我们在5月9日开始进入湖区,有(yǒu)一个七人(qīrén)探路小分队,自北往南纵贯罗布泊湖底。湖表面已没有水,有些地面松软陷车,有些地面则比较平整。汽车车胎由于锋利的盐晶块切割,损耗过大,无法继续前进。”
那天晚上,考察队只能原地宿营。因为当时(dāngshí)所带的汽油和水(shuǐ)都消耗了不少,彭加木只得决定原路返回,重新补充油、水之后再度前进。
湖底的(de)盐晶块是前进的极大阻碍,最终用来给考察队(kǎocháduì)开路的,竟然是队员们手中十几(shíjǐ)磅重的大铁锤。这个方法也是彭加木提出(tíchū)的,最初遭到队员们的一致反对,大家认为在罗布泊湖底用铁锤人工开路简直是天方夜谭。
事实证明(shìshízhèngmíng),彭加木的意见是正确的。5月30日,考察队重新出发,又一次到了这个地区,大家拿着铁锤下车,一锤一锤地把车轮前的盐晶块(yánjīngkuài)砸碎。汽车(qìchē)颠簸前行,直到他们找到了古河道的入湖口,路(lù)才一下子平顺了起来,盐晶块对车行的阻碍得以解除。
汽车沿着古河道走了两天,终于完成了纵贯罗布泊的计划。沿途(yántú),考察队进行了简单的地质勘探,彭加木凿开盐壳,从下面瓦蓝色(lánsè)的沙层中取出一个水样(shuǐyàng),兴奋地对大家说:“这里可能有‘重水’!”能够在地域广阔的罗布泊找到重水资源,这无疑(wúyí)是(shì)对中国核物理工业发展的一个巨大贡献。
彭加木曾这样评价此次纵穿罗布泊的(de)经历(jīnglì):“此次胜利的穿越盐壳地带,自北而南纵贯罗布泊干涸湖底(húdǐ)成功,是一个很大的收获,这是前所未有的,对罗布泊洼地中心区域已经有了一些了解,可算(kěsuàn)得是敲开了罗布泊的大门。”
考察队在6月5日到达(dàodá)了考察的最后一站——米兰农场。
进入米兰(mǐlán)农场(nóngchǎng)以后,考察队的队员们如同卸下了千斤重担。按原定的方案,在米兰农场休息几天后考察队就可以启程回乌鲁木齐了。
就在此时,彭加木突然向队员们提出了(le)“东进计划”。
这次考察原计划到7月3日结束,还有近一个月时间。彭加木建议(jiànyì)暂不回乌鲁木齐,利用剩下的这些时间一鼓作气(yīgǔzuòqì)完成对(duì)整个罗布泊地区的考察。
1979年冬天,彭加木作为纪录片《丝绸之路》的“先遣队”成员之一,曾完成了对罗布泊西部的考察(kǎochá),这次,考察队又从罗布泊的中部纵穿(zòngchuān)而过,他计划在余下一个月(yígèyuè)的时间里,沿罗布泊东部北上,穿过疏流河(liúhé)直至敦煌,完成对罗布泊地区的全面考察,最后再(zài)回乌鲁木齐。
虽然队员们已经非常疲惫,但最终大家还是(háishì)决定采纳彭加木的建议。
彭加木通过电报向中科院新疆分院(fēnyuàn)汇报请求批准。新疆分院接到电报后,经研究同意他们的计划,但(dàn)一再嘱咐(yīzàizhǔfù),一定要注意安全,有情况及时与基地联系。
在准备出发,装(zhuāng)汽油和水的时候,彭加木提议可以多装一桶汽油,少装一桶水。原因是从地图上看,到了库木库都克这个地方(dìfāng)有水井(shuǐjǐng),可以在这个地方补充水源。根据路程(lùchéng)计算,到库木库都克只有400多公里,最多两天即可赶到。
然而,在这一段路上,考察队(kǎocháduì)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麻烦。
6月11日,考察队一早从米兰出发,一直赶路到天黑。十几个小时,车子只走了(le)58公里(lǐ),还不到计划行程的(de)一半。一路都是松软的沙石地,三辆车不是这辆陷进了泥坑,就是那辆困(kùn)在了沙窝子,有时候几个小时才能把一辆车从泥坑里弄出来,此后的几天里也都是如此,结果,本来预计两天的路程考察队走了整整(zhěngzhěng)6天。
6月16日下午6时左右,考察队终于赶到(gǎndào)了库木库都克,此时大家都已是筋疲力尽,却不得不再次外出——由于行程(xíngchéng)被耽搁,出发时带的汽油和水此时都快要消耗(xiāohào)殆尽了。
“库木库都克”是维吾尔语(wéiwúěryǔ)“沙井”的意思。从考察队带的那张地图看,这里确实标有水井。考察队支好帐篷,休息了一会儿(yīhuìer),便立刻出发去找水(zhǎoshuǐ)。
让彭加木和队员们大为失望的是,从下午找到晚上,这片茫茫的沙漠中根本没有水(shuǐ)井的踪影。眼下,所剩的汽油只能供三辆(sānliàng)车行驶几十公里;水,则只剩下一汽油桶,且(qiě)已变质,难以饮用。
没有水和汽油,考察队员们即刻就面临生命危险,几乎陷入绝境的(de)考察队决定向部队紧急求助(qiúzhù)。
6月16日晚上10时10分,彭加木亲自起草了发给部队的告急电报:“我们已到(dào)达了库木库都克以西大约十公里。我们缺油和水(shuǐ),请求紧急(jǐnjí)支援油、水各500公斤,现有的水只能维持到18日。”
电报发出后(hòu),正在大家焦急等待回复的时候(shíhòu),彭加木提出了新的建议。
一向节俭的彭加木认为,用直升机运水(yùnshuǐ)太贵了(le)。直升机飞行一小时,在那个年代要花2000多块钱,从驻军基地到宿营地,来回(láihuí)要飞好几个小时。他建议大家自力更生,尽量自己找水。
不久前,他和别人闲聊中听说,年初的时候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曾经在“八一泉(quán)”加过(jiāguò)水。“八一泉”位于疏流河故道北岸,在库木库都克东北约30公里处(chù)。
所以,彭加木建议开车(kāichē)再(zài)往东面去找一次水井,但是这个建议遭到了(le)队员们的全体反对。大家计算了一下,这一路线要用掉(diào)大概半桶汽油,大家一致认为不能再消耗本已不多的汽油,应该等与部队联系上以后,再作打算。
第二天上午(shàngwǔ)11点半,考察队收到了部队发来的电报:“飞机18日到库木库都克送水(shuǐ),你们不要动,原地待命。”
接到电报(diànbào),大家都很兴奋。队员汪文先想把这一喜讯告诉(gàosù)彭加木,他拿着电文走出帐篷,却没有看到彭加木的身影。
他以为彭加木只是去附近解手了,于是又回帐篷(zhàngpéng)等待。一个小时后还未见彭加木回来,大家方(fāng)感觉有些不妙了。
此时,司机(sījī)王万轩(wángwànxuān)走出帐篷,到汽车上去取衣服。他突然发现右边的座位上有一张摊开的地图。这张地图是全队唯一一张地形图,彭加木一路上一直坐在这个(zhègè)位置,他是从不把这张地图随意丢放的。
王万轩把地图(dìtú)拿起收好,突见地图下面有一张纸条,上面写道:
“我往东去找水井(shuǐjǐng)。彭,17/6 10:30”
卫星(wèixīng)拍下的“地球之耳”罗布泊。
罗布泊的(de)神秘之处,并不仅仅在于它奇特(qítè)的地理构造,更源于它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湮灭在漫漫黄沙下的历史传说。
罗布泊历史上最繁华的一个时期,是在“楼兰(lóulán)王国”兴盛之时。楼兰古城地处罗布泊的西北侧,这里曾经(céngjīng)是丝绸之路南支的咽喉门户。
楼兰于公元前176年以前(yǐqián)建国、公元630年消亡,历时800多年。随着(suízhe)楼兰国的消亡,这里渐渐成为人迹罕至之地,丝绸之路的故道不复存在,罗布荒原逐渐被人们所遗忘(yíwàng)。
直到1900年3月,瑞典探险家斯文(sīwén)·赫定探险队沿着干枯的孔雀河左河床来到罗布荒原,意外(yìwài)地发现了隐藏在历史(lìshǐ)沙砾中一千多年的楼兰古城,这一“神迹”才重现于世。
斯文·赫定回到欧洲,向全世界公布了罗布荒原上的(de)“沙埋文明”,轰动一时。神秘的“楼兰(lóulán)”是(shì)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成就之一,而楼兰古国所在(suǒzài)的这一片罗布荒原,成为了世界探险家趋之若鹜的神秘地带。
斯文·赫定曾在他那部著名的《亚洲腹地探险8年》一书中写道:“罗布泊使我惊讶,它像座仙湖(xiānhú),水面像镜子一样,在和煦的阳光(yángguāng)下,我乘舟而行,如(rú)神仙一般。”
作为此地最大的(de)沙漠咸湖,罗布泊也因此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。
上世纪初叶,罗布泊的“游移之谜(zhīmí)”曾引起世界学术界的极大争论。
最早(zuìzǎo)到新疆(xīnjiāng)考察的中外科学家们曾对罗布泊(luóbùpō)的确切位置争论不休,斯文·赫定认为罗布泊存在南北湖区,由于(yóuyú)入湖河水带有大量泥沙,沉积后抬高了湖底,原来的湖水就自然向另一处更低的地方流去,又过许多年,抬高的湖底会由于风蚀再次降低,湖水再度回流,这个周期为1510年,所以(suǒyǐ),他认为罗布泊是一个在沙漠中不断游移的湖。
斯文·赫定这(zhè)一学说,在(zài)当时曾得到(dédào)了世界普遍认可。“游移之谜”给罗布泊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,这片幽灵般的湖泊,再一次引起了全世界探险家的极大兴趣。
1927年,中国科学家第一次靠近(kàojìn)了这片“幽灵湖泊”。斯文·赫定在筹备第六次中亚考察时,决定由中瑞两国共同(gòngtóng)组成一个(yígè)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。时任北京大学教务长的知名学者徐炳旭(xúbǐngxù)担任中方团长,团中尽数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专家,如地质与古生物学家丁道衡、考古学家黄文弼、地理学家(dìlǐxuéjiā)陈宗器等。
这次考察从1927年持续到1933年,考察队先后在罗布泊、吐鲁番和塔里木盆地(tǎlǐmùpéndì)进行考古调查(diàochá)和部分试掘,撰写了《罗布淖尔考古记(jì)》、《吐鲁番考古记》、《塔里木盆地考古记》等,在国内出版,引起很大反响(fǎnxiǎng)。
此后的(de)很长一段时间,罗布泊的研究湮灭于连年战火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9年,罗布荒原终于又(yòu)迎来了一支新的科学考察队。
从1956年到1959年,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(zōnghé)考察队对塔里木下游和罗布泊地区(dìqū)进行了新中国成立后最大规模的一次综合考察,当时,队员们是乘着舟进入(jìnrù)罗布泊的。
夏训诚因被分在北疆(běijiāng)组考察,遗憾地与当时(dāngshí)尚未干涸的(de)罗布泊失之交臂。他说,那次考察留下了人类在罗布泊荡舟的最后记录,“由于1952年在拉依河筑坝,使塔里木河和孔雀河(kǒngquèhé)彻底分流,孔雀河下泄的河水逐渐断绝,罗布泊在上世纪(shìjì)70年代初全部干涸了,终结了它作为一个湖泊的历史。”
那次考察后不久,罗布泊被定为核试验场,从此成为军事禁区。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,任何与核试验无关的人都不得进入(jìnrù)这个地区(dìqū)。
彭加木也没有参加(cānjiā)那次考察。那时他正在上海(shànghǎi)的医院中,与恶性肿瘤、癌细胞搏斗着。
“彭加木”这个名字,也刚刚出现(chūxiàn)不久。
1947年,22岁的广东番禺青年彭家睦从中央大学(1949年更名(gēngmíng)南京大学)农学院毕业,到(dào)北京大学农学院任教,专攻农业化学。1949年,他被分配(fēnpèi)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。
1956年初,中央发出了“向(xiàng)科学进军”的号召,正当(zhèngdāng)此时,彭家睦迎来了一个对他个人发展千载难逢的机会。
科学院的领导研究决定,派年轻的彭家睦到莫斯科(mòsīkē)去(qù)学习一项新的技术——核磁共振,办理完出国手续即刻便要动身。
能够去苏联学习,无疑是一个好机会,彭家睦自然是高兴极了,但是他(tā)马上又(yòu)陷入了两难的选择中。
就在这个当口,中国科学院为了开发祖国边疆的丰富资源,组织了综合考察委员会。这个委员会此时正在“招兵买马(zhāobīngmǎimǎ)”,吸收各方面(fāngmiàn)科技人才,准备(zhǔnbèi)组成若干小组,分赴祖国边疆各地进行实地考察。
究竟是去国外留学还是去边疆考察,31岁的彭家(péngjiā)睦面临重要的人生选择,经过反复(fǎnfù)考虑后,他选择了后者。
彭家睦曾经亲笔写下作出这一选择的(de)(de)原因:“我必须在出国和到边疆之间立刻做出选择,我考虑的结果,认为出国学习的任务虽然重要,但可以由别的同志来完成,别的同志也乐于去(qù)干(gàn),为了让科学在祖国遍地开花,作为一个共产党员,应当选择到最艰苦的地方去。”
在同样(tóngyàng)毕业于南京大学的(de)夏训诚看来,彭家睦当年的选择着实令人敬佩:“上海的科研条件自然(zìrán)比边疆要好得多,而且他当时在植物学领域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,但是为了边疆的科研,他甘愿(gānyuàn)做铺路石子。”
1956年3月, 彭家睦的申请正式得到了批准,他如愿以偿地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(shēngwùhuàxué)研究所调到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工作(gōngzuò),当时的职务是助理(zhùlǐ)研究员。
此时,他的户口也从上海迁到了北京(běijīng)。在(zài)迁户口时,彭家睦打(dǎ)了一个改名报告,把“彭家睦”改为了“彭加木”。从此,他一直用“彭加木”这个名字。
实际上,在迁户口之前,他就已经在使用“彭加木”的名字了。为了争取参加中(zhōng)国边疆科考,彭加木直接写信给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。他在信中(xìnzhōng)写道:“我具有从荒野中踏出一条(yītiáo)道路(dàolù)的勇气。”在信的末尾,署名并不是“彭家睦”,而是“彭加木”。
从“彭家睦”到“彭加木”,其实是他表示“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”的决心。彭加木认为“家睦”只是希望家庭和睦,着眼于(zhuóyǎnyú)小家(xiǎojiā),太狭隘(xiáài)了;他要跳出小家庭,为边疆“添草加木”。
那一年的秋天,彭加木第一次来到(láidào)乌鲁木齐。当时(dāngshí)新疆的科研事业只是有了一点点萌芽,而在生物化学研究方面几乎是一个空白。一到新疆,彭加木就帮助当地筹建了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。然而(ránér),这个豪情万丈的垦荒者,却突然遭受了一个重大打击(dǎjī)。
1957年初,彭加木突然被查出患有纵隔障恶性肿瘤,返回上海治疗。以当时的医疗条件,医生们根据(gēnjù)有限的医学文献和病例判断(pànduàn),彭加木最多只能(zhǐnéng)活两年。
祸不单行的是,在住院期间,彭加木又(yòu)被查出还患有另一种恶性肿瘤——网状细胞(xìbāo)淋巴瘤,患这种病一般只能活几个月。
等于是被判了死刑的彭加木却没有(méiyǒu)被病魔打倒(dǎdǎo),一年以后,他竟然奇迹般地康复了。虽然医生严令禁止他离开上海(shànghǎi),但是彭加木刚一出院就接二连三地要求“放虎归山”,回到新疆去工作。
1958年的春天,一个险些被癌症夺去生命的人,又踏上了西行(xīxíng)的旅程,彭加木与罗布泊也从此正式(zhèngshì)结缘。
彭加木在新疆工作期间,一共有过四次对(duì)新疆地区的大规模考察(kǎochá)。这些考察包括人文、地理、生物、矿产资源、文物古籍、风土民情等。
1959年,彭加木(péngjiāmù)曾到过罗布泊北部地区,采集过土壤标本。经过化验,他发现此地土壤中的(de)钾含量(hánliàng)非常高。1964年,他对流入罗布泊的孔雀河、塔里木河、车尔臣河等河流进行了综合考察。参与这次考察的共有四个人(rén),由彭加木带队(dàiduì),此外还有新疆化学所的两名科研工作者和一名司机。考察从9月上旬到10月下旬,历时40多天,行程近5000公里(gōnglǐ)。
在(zài)对流入罗布泊的(de)几条河的钾含量作了初步分析后,彭加木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——罗布泊极有可能蕴藏巨大储量的钾盐。
钾盐是农用钾肥的生产原料,在我国属大宗紧缺(jǐnquē)矿种,中国(zhōngguó)境内可溶性钾盐资源严重不足,需要大量进口。
彭加木同时判断,在罗布泊的(de)盐层中,还含有宝贵的原料,比如制造(zhìzào)飞机所需的镁,稀有金属锂(lǐ)等。另外,那里还可能有重水资源。重水是重要的中子减速器,无论是建造原子能反应堆还是制造原子弹都会用到它(tā),此外,它还是制造氢弹的原料,属于重要的战略资源。
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,我国(wǒguó)在钾盐勘查方面投入(tóurù)大量(dàliàng)的人力和经费,除了在柴达木盆地取得重大突破外,其它(qítā)地区成果甚微,以致出现了中国“无钾论”的看法。中国是否能再找到大型钾盐矿床,一直是科学界关注的焦点。
那次考察中,在塔里木河下游,彭加木发现河水(héshuǐ)的(de)钾含量在逐渐增加。他根据气象资料推算出河水的流量,并从河水的流量数据(shùjù)推算出河流搬运钾元素的大约值,由此(yóucǐ)估算出罗布泊每年会积聚约75万吨钾,可能还含有其他稀有金属和重水等资源。
夏训诚说,彭加木是(shì)第一个提出罗布泊有钾盐矿(kuàng)的(de)人。如果罗布泊果真富集钾盐矿,这里就不再是人迹罕至的荒漠,而是一个巨大的“聚宝盆”。
在新疆进行这一次考察时,彭加木39岁,在罗布泊寻找钾盐矿成为了他对这片神秘(shénmì)区域最初的研究目标。遗憾(yíhàn)的是,由于“文革”的影响,他对罗布泊的研究计划(jìhuà)也不得不搁浅了十余年。
“地球之耳”的(de)神秘大门对彭加木再次打开的时候,他已经54岁了(le)。对一个科学家来说,这个年龄还(hái)算年轻。然而,重新走进这道大门仅仅一年时间,彭加木的生命戛然而止。
1979年的(de)冬天,刚刚率领科学考察队从(cóng)天山最高峰——托木尔峰归来的夏训诚,突然接到新疆考古所副所长穆舜英打来的电话。
穆舜英在电话中说,由中日联合组成的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即将(jíjiāng)来新疆,在罗布泊(luóbùpō)附近进行(jìnxíng)实地拍摄。夏训诚被聘请为“顾问”,要组成一个“先遣队”进入罗布泊打个前站。
罗布泊在上世纪60年代(niándài)被列为军事禁区,又因“文革”的关系,此地的科学考察一直处于停滞状态。对夏(duìxià)训诚来说,能够再次进入罗布泊就像是“圆梦”一样,兴奋之余,他突然想到(xiǎngdào)了老朋友彭加木。
致力于沙漠治理的夏训诚从上(shàng)世纪50年代起就一直在新疆进行考察和研究,因工作关系与彭加木(péngjiāmù)结识多年,“我知道他一直想去罗布泊找钾盐,这个机会千载难逢(qiānzǎinánféng)。”夏训诚说。
于是,他(tā)把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告诉了(le)彭加木,彭加木当时竟高兴得跳了起来,连说“太好了(tàihǎole)”。夏训诚现在仍然记得,彭加木当时像孩子一样握着他的手,一直恳求他帮忙,与有关单位(dānwèi)联系参加这次考察。
夏训诚回忆,当时联系的过程颇为复杂,罗布泊毕竟是几十年的军事禁区。“据我了解,《丝绸之路(sīchóuzhīlù)》摄制组此行进入(jìnrù)罗布泊,是邓小平(dèngxiǎopíng)同志亲自(qīnzì)批准的。”最终,执着的彭加木还是得到了这次进入罗布泊的机会。
“先遣队”不是一个(yígè)严格(yángé)的科学考察的组织,但是每(měi)一个队员都有自己心里的“小算盘”,作为地理工作者,夏训诚关注罗布泊的自然环境变迁情况;而对于彭加木来说,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延续上世纪60年代未完成的考察计划,在罗布泊寻找钾盐(jiǎyán)。
这是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,罗布泊(luóbùpō)地(dì)区第一次向非军事人员开放。20余天的时间(shíjiān)里,6辆吉普车组成的车队穿过了沉寂的荒原,穿过楼兰古城和白龙堆雅丹,在完成了几次横向与纵向穿插罗布泊西部的考察后,“先遣队”成功地回到了乌鲁木齐的基地(jīdì)。
在离开基地的前一天(qiányītiān),彭加木向夏训诚提议,由他俩(tāliǎ)牵头,上书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建议正式组建考察队,对罗布泊进行(jìnxíng)全面的综合考察。
彭加木此时提出考察计划,已(yǐ)不仅仅(bùjǐnjǐn)为了他寻找已久的钾盐矿。一个多世纪以来(yǐlái),俄国人、瑞典人、日本人一次一次来到罗布泊(luóbùpō)考察、探险,写出了许多关于罗布泊的文章,以至于国外竟有一种言论:“罗布泊在中国,而罗布泊的研究在外国”。彭加木向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表示,要夺回中国科学家在罗布泊的发言权。
几天以后,彭加木正式调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,这无疑对(duì)组建罗布泊考察队起到了积极的(de)作用。
1980年初(niánchū),通过各方面的努力,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(fēnyuàn)正式下达了成立(chénglì)罗布泊科学考察队的文件,并决定由彭加木担任队长,夏训诚担任副队长。
彭加木心中多年的夙愿,即将(jíjiāng)达成。
根据计划(jìhuà),这次对罗布泊的综合考察分三次进行。1980年的第一次考察主要(zhǔyào)是路线考察,时间定在1980年的5、6月间,第二年再进行后两次(liǎngcì)考察。
“第一次考察之所以(zhīsuǒyǐ)定在(zài)这个月份,是因为这时正是沙漠荒原风沙季节和酷热季节的‘空档’。”夏训诚说。但是他认为当时的计划并(bìng)不周全,“我们当时不知道,实际上罗布泊地区(dìqū)并没有这种‘空档’,或者说很短促。”
在制定计划的同时,考察队正式开始“招兵买马”。夏训诚主持组建队伍的工作,他从新疆分院的好几个部门抽调了6名专业(zhuānyè)人员和3名司机、一名后勤(hòuqín),这十位同志组成(zǔchéng)了一支罗布泊科学考察队。
5月3日,由彭加木率队,罗布泊(luóbùpō)科学考察队从乌鲁木齐出发,正式向罗布泊进发了(le)。因为在出发前突然接到去美国考察的通知,夏训诚遗憾地(dì)错过了参加第一次路线考察的机会。
夏训诚直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,建议组建考察队时,彭加木曾悲愤地说(dìshuō):“我不希望在罗布泊全是外国人(wàiguórén)留下的足迹,作为一个中国人,我就觉得应该把自己的骨头(gútou)埋在罗布泊,使它的土壤多一点(duōyìdiǎn)中国的有机质!”
这不是一句玩笑,而是彭加木(péngjiāmù)的真实想法。如果说科学探索总(zǒng)需要牺牲,他是在进入罗布泊之前,就已经作好了牺牲准备的。
夏训诚万万没有想到,仅仅一个多月以后,彭加木的话(dehuà)一语成谶。
作为对罗布泊的(de)第一次深入性考察,彭加木的计划是十分大胆的。
他打算率队从北至南,纵穿(zòngchuān)罗布泊。在他看来,只有纵穿罗布泊,才能弄清这个神秘之地(zhīdì)的真实面目。
但是(dànshì),第一次纵穿并未成功。彭加木(péngjiāmù)在日记中写道:“我们在5月9日开始进入湖区,有(yǒu)一个七人(qīrén)探路小分队,自北往南纵贯罗布泊湖底。湖表面已没有水,有些地面松软陷车,有些地面则比较平整。汽车车胎由于锋利的盐晶块切割,损耗过大,无法继续前进。”
那天晚上,考察队只能原地宿营。因为当时(dāngshí)所带的汽油和水(shuǐ)都消耗了不少,彭加木只得决定原路返回,重新补充油、水之后再度前进。
湖底的(de)盐晶块是前进的极大阻碍,最终用来给考察队(kǎocháduì)开路的,竟然是队员们手中十几(shíjǐ)磅重的大铁锤。这个方法也是彭加木提出(tíchū)的,最初遭到队员们的一致反对,大家认为在罗布泊湖底用铁锤人工开路简直是天方夜谭。
事实证明(shìshízhèngmíng),彭加木的意见是正确的。5月30日,考察队重新出发,又一次到了这个地区,大家拿着铁锤下车,一锤一锤地把车轮前的盐晶块(yánjīngkuài)砸碎。汽车(qìchē)颠簸前行,直到他们找到了古河道的入湖口,路(lù)才一下子平顺了起来,盐晶块对车行的阻碍得以解除。
汽车沿着古河道走了两天,终于完成了纵贯罗布泊的计划。沿途(yántú),考察队进行了简单的地质勘探,彭加木凿开盐壳,从下面瓦蓝色(lánsè)的沙层中取出一个水样(shuǐyàng),兴奋地对大家说:“这里可能有‘重水’!”能够在地域广阔的罗布泊找到重水资源,这无疑(wúyí)是(shì)对中国核物理工业发展的一个巨大贡献。
彭加木曾这样评价此次纵穿罗布泊的(de)经历(jīnglì):“此次胜利的穿越盐壳地带,自北而南纵贯罗布泊干涸湖底(húdǐ)成功,是一个很大的收获,这是前所未有的,对罗布泊洼地中心区域已经有了一些了解,可算(kěsuàn)得是敲开了罗布泊的大门。”
考察队在6月5日到达(dàodá)了考察的最后一站——米兰农场。
进入米兰(mǐlán)农场(nóngchǎng)以后,考察队的队员们如同卸下了千斤重担。按原定的方案,在米兰农场休息几天后考察队就可以启程回乌鲁木齐了。
就在此时,彭加木突然向队员们提出了(le)“东进计划”。
这次考察原计划到7月3日结束,还有近一个月时间。彭加木建议(jiànyì)暂不回乌鲁木齐,利用剩下的这些时间一鼓作气(yīgǔzuòqì)完成对(duì)整个罗布泊地区的考察。
1979年冬天,彭加木作为纪录片《丝绸之路》的“先遣队”成员之一,曾完成了对罗布泊西部的考察(kǎochá),这次,考察队又从罗布泊的中部纵穿(zòngchuān)而过,他计划在余下一个月(yígèyuè)的时间里,沿罗布泊东部北上,穿过疏流河(liúhé)直至敦煌,完成对罗布泊地区的全面考察,最后再(zài)回乌鲁木齐。
虽然队员们已经非常疲惫,但最终大家还是(háishì)决定采纳彭加木的建议。
彭加木通过电报向中科院新疆分院(fēnyuàn)汇报请求批准。新疆分院接到电报后,经研究同意他们的计划,但(dàn)一再嘱咐(yīzàizhǔfù),一定要注意安全,有情况及时与基地联系。
在准备出发,装(zhuāng)汽油和水的时候,彭加木提议可以多装一桶汽油,少装一桶水。原因是从地图上看,到了库木库都克这个地方(dìfāng)有水井(shuǐjǐng),可以在这个地方补充水源。根据路程(lùchéng)计算,到库木库都克只有400多公里,最多两天即可赶到。
然而,在这一段路上,考察队(kǎocháduì)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麻烦。
6月11日,考察队一早从米兰出发,一直赶路到天黑。十几个小时,车子只走了(le)58公里(lǐ),还不到计划行程的(de)一半。一路都是松软的沙石地,三辆车不是这辆陷进了泥坑,就是那辆困(kùn)在了沙窝子,有时候几个小时才能把一辆车从泥坑里弄出来,此后的几天里也都是如此,结果,本来预计两天的路程考察队走了整整(zhěngzhěng)6天。
6月16日下午6时左右,考察队终于赶到(gǎndào)了库木库都克,此时大家都已是筋疲力尽,却不得不再次外出——由于行程(xíngchéng)被耽搁,出发时带的汽油和水此时都快要消耗(xiāohào)殆尽了。
“库木库都克”是维吾尔语(wéiwúěryǔ)“沙井”的意思。从考察队带的那张地图看,这里确实标有水井。考察队支好帐篷,休息了一会儿(yīhuìer),便立刻出发去找水(zhǎoshuǐ)。
让彭加木和队员们大为失望的是,从下午找到晚上,这片茫茫的沙漠中根本没有水(shuǐ)井的踪影。眼下,所剩的汽油只能供三辆(sānliàng)车行驶几十公里;水,则只剩下一汽油桶,且(qiě)已变质,难以饮用。
没有水和汽油,考察队员们即刻就面临生命危险,几乎陷入绝境的(de)考察队决定向部队紧急求助(qiúzhù)。
6月16日晚上10时10分,彭加木亲自起草了发给部队的告急电报:“我们已到(dào)达了库木库都克以西大约十公里。我们缺油和水(shuǐ),请求紧急(jǐnjí)支援油、水各500公斤,现有的水只能维持到18日。”
电报发出后(hòu),正在大家焦急等待回复的时候(shíhòu),彭加木提出了新的建议。
一向节俭的彭加木认为,用直升机运水(yùnshuǐ)太贵了(le)。直升机飞行一小时,在那个年代要花2000多块钱,从驻军基地到宿营地,来回(láihuí)要飞好几个小时。他建议大家自力更生,尽量自己找水。
不久前,他和别人闲聊中听说,年初的时候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曾经在“八一泉(quán)”加过(jiāguò)水。“八一泉”位于疏流河故道北岸,在库木库都克东北约30公里处(chù)。
所以,彭加木建议开车(kāichē)再(zài)往东面去找一次水井,但是这个建议遭到了(le)队员们的全体反对。大家计算了一下,这一路线要用掉(diào)大概半桶汽油,大家一致认为不能再消耗本已不多的汽油,应该等与部队联系上以后,再作打算。
第二天上午(shàngwǔ)11点半,考察队收到了部队发来的电报:“飞机18日到库木库都克送水(shuǐ),你们不要动,原地待命。”
接到电报(diànbào),大家都很兴奋。队员汪文先想把这一喜讯告诉(gàosù)彭加木,他拿着电文走出帐篷,却没有看到彭加木的身影。
他以为彭加木只是去附近解手了,于是又回帐篷(zhàngpéng)等待。一个小时后还未见彭加木回来,大家方(fāng)感觉有些不妙了。
此时,司机(sījī)王万轩(wángwànxuān)走出帐篷,到汽车上去取衣服。他突然发现右边的座位上有一张摊开的地图。这张地图是全队唯一一张地形图,彭加木一路上一直坐在这个(zhègè)位置,他是从不把这张地图随意丢放的。
王万轩把地图(dìtú)拿起收好,突见地图下面有一张纸条,上面写道:
“我往东去找水井(shuǐjǐng)。彭,17/6 10:30”
 彭加木失踪前留下的最后一张(yīzhāng)字条。
纸条显然是这天上午写下的,日(rì)期上的“17”日还是“16”日改写的,大概是彭加木曾经一时写错了日期。此时大家(dàjiā)才发现,彭加木的黄帆布包和(hé)那只能装两公斤水的水壶也不见了。
队员(duìyuán)们怎么也想不到,这张字条,竟是彭加木(péngjiāmù)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。
那天下午,所有队员出动寻找彭加木,他们按照(ànzhào)字条的指引向东寻,沿着彭加木那双42号翻毛皮靴在沙地中留下的脚印走了将近8公里,都不见他的踪影。脚印却(què)最终消失在盐(yán)壳地的边缘,搜寻(sōuxún)一下子失去了方向。
为了(le)跟部队及时电报联系,队员们只得在晚上10点回到了营地,大家在营地里燃起篝火,把吉普车开到最高处,向东方开亮(kāiliàng)了车前大灯,并每隔一小时(xiǎoshí)向空中发射一次信号弹。
队员们希望,彭加木可以循着亮光,找到(zhǎodào)营地的方向。
然而,彭加木消瘦的身影再也(zàiyě)没有出现在队员们的视线中。
6月18日凌晨两点,考察队(kǎocháduì)正式(zhèngshì)发出电报:彭加木走失,下落不明。
此时,距离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已经过去了16个小时。
18日中午,直升机载着500公斤水找到了考察队的露营地,队员们(men)获救了。第二天,部队又(yòu)给他们送来三桶汽油。但是,经过队员们持续十几个小时的寻找,没有任何(rènhé)结果。
搜寻中唯一的突破,是在一片岩石间(jiān)发现了一张椰子奶油糖的糖纸,旁边(pángbiān)还有人坐过的痕迹。队友们知道,这个牌子的奶油糖是彭加木随身携带的,但是沿着旁边的脚印(jiǎoyìn)追踪了几十公里后(hòu),脚印又在盐壳边缘消失了。
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于6月18日下午6点得到了彭加木失踪的消息。晚上12点,副院长(yuànzhǎng)陈善明带着两名干部,由两个司机轮流开车连夜往马兰基地(jīdì)(jīdì)赶。19日早晨7点一到基地,他就会同基地的几位领导(lǐngdǎo)组成了救援领导小组,组织对彭加木的救援工作。
一个大规模的寻找彭加木的战役拉开了(le)帷幕。
根据夏训诚的回忆,当年较大规模的寻找,一共有四次(sìcì)。
第一次寻找(xúnzhǎo)是在彭加木刚失踪时,6月18日到19日,队员们在宿营地周围(zhōuwéi)进行了搜寻。
第二次寻找是在6月(yuè)20日到26日,在收到(shōudào)呼救讯号后,当地部队和科考(kēkǎo)队员出动136人次,空军出动9架直升机、三架“安-2”型飞机,在出事地点东西50公里范围内进行地毯式低空搜寻。
第三次寻找是(shì)在7月(yuè)7日到8月2日,117人,48辆车,29架次飞机,搜索面积达到4000多平方公里。
“我参加的就是第三次(dìsāncì)搜寻,当时公安人员(gōngānrényuán)还特意带着六条警犬(jǐngquǎn)赶到了罗布泊。”夏训诚说,可惜因为当地天气太热,警犬也丧失了嗅觉,并没有找到彭加木的踪迹。
就在人们对彭加木的生还(shēnghuán)已经(yǐjīng)基本丧失了希望的时候,一家香港媒体竟然曝出新闻:失踪的彭加木在美国出现了。
彭加木失踪前留下的最后一张(yīzhāng)字条。
纸条显然是这天上午写下的,日(rì)期上的“17”日还是“16”日改写的,大概是彭加木曾经一时写错了日期。此时大家(dàjiā)才发现,彭加木的黄帆布包和(hé)那只能装两公斤水的水壶也不见了。
队员(duìyuán)们怎么也想不到,这张字条,竟是彭加木(péngjiāmù)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。
那天下午,所有队员出动寻找彭加木,他们按照(ànzhào)字条的指引向东寻,沿着彭加木那双42号翻毛皮靴在沙地中留下的脚印走了将近8公里,都不见他的踪影。脚印却(què)最终消失在盐(yán)壳地的边缘,搜寻(sōuxún)一下子失去了方向。
为了(le)跟部队及时电报联系,队员们只得在晚上10点回到了营地,大家在营地里燃起篝火,把吉普车开到最高处,向东方开亮(kāiliàng)了车前大灯,并每隔一小时(xiǎoshí)向空中发射一次信号弹。
队员们希望,彭加木可以循着亮光,找到(zhǎodào)营地的方向。
然而,彭加木消瘦的身影再也(zàiyě)没有出现在队员们的视线中。
6月18日凌晨两点,考察队(kǎocháduì)正式(zhèngshì)发出电报:彭加木走失,下落不明。
此时,距离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已经过去了16个小时。
18日中午,直升机载着500公斤水找到了考察队的露营地,队员们(men)获救了。第二天,部队又(yòu)给他们送来三桶汽油。但是,经过队员们持续十几个小时的寻找,没有任何(rènhé)结果。
搜寻中唯一的突破,是在一片岩石间(jiān)发现了一张椰子奶油糖的糖纸,旁边(pángbiān)还有人坐过的痕迹。队友们知道,这个牌子的奶油糖是彭加木随身携带的,但是沿着旁边的脚印(jiǎoyìn)追踪了几十公里后(hòu),脚印又在盐壳边缘消失了。
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于6月18日下午6点得到了彭加木失踪的消息。晚上12点,副院长(yuànzhǎng)陈善明带着两名干部,由两个司机轮流开车连夜往马兰基地(jīdì)(jīdì)赶。19日早晨7点一到基地,他就会同基地的几位领导(lǐngdǎo)组成了救援领导小组,组织对彭加木的救援工作。
一个大规模的寻找彭加木的战役拉开了(le)帷幕。
根据夏训诚的回忆,当年较大规模的寻找,一共有四次(sìcì)。
第一次寻找(xúnzhǎo)是在彭加木刚失踪时,6月18日到19日,队员们在宿营地周围(zhōuwéi)进行了搜寻。
第二次寻找是在6月(yuè)20日到26日,在收到(shōudào)呼救讯号后,当地部队和科考(kēkǎo)队员出动136人次,空军出动9架直升机、三架“安-2”型飞机,在出事地点东西50公里范围内进行地毯式低空搜寻。
第三次寻找是(shì)在7月(yuè)7日到8月2日,117人,48辆车,29架次飞机,搜索面积达到4000多平方公里。
“我参加的就是第三次(dìsāncì)搜寻,当时公安人员(gōngānrényuán)还特意带着六条警犬(jǐngquǎn)赶到了罗布泊。”夏训诚说,可惜因为当地天气太热,警犬也丧失了嗅觉,并没有找到彭加木的踪迹。
就在人们对彭加木的生还(shēnghuán)已经(yǐjīng)基本丧失了希望的时候,一家香港媒体竟然曝出新闻:失踪的彭加木在美国出现了。
 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地纪念碑前的纪念。
1980年10月11日(rì),香港《中报》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载了一则奇闻(qíwén)。
文中称,当年9月14日下午7时许,一个名叫周光磊(zhōuguānglěi)的“中国(zhōngguó)留美学者”和几名朋友在(zài)华盛顿的一家饭馆吃饭的时候,竟然看见了在罗布泊失踪半年之久的著名科学家——彭加木。
这篇写得有鼻子有眼的(de)“奇闻”立刻引起海内外一片哗然。为了澄清事实,新华社记者专门(zhuānmén)就此事进行了调查,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明确(míngquè)表示,她和彭加木从来就不认识周光磊这个人。
新华社记者的调查(diàochá)虽然揭穿了所谓“周光磊”编造的谎言,但关于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的原因,一时间出现了很多以讹传讹的坊间版本。
当时流传最广的,是说彭加木从罗布泊秘密逃亡美国(měiguó)或者苏联。
在夏训诚看来,这样的(de)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,“营地附近都(dōu)有军事雷达,怎么可能美国或者(huòzhě)苏联的飞机把他接走,我们的部队能不发现?”
在《追寻彭加木》一书中,叶永烈回忆,当年年底由国家组织的第四次对彭加木的搜寻(sōuxún),在某种意义上也有澄清流言的目的,如果能够找到彭加木的遗体,就能够击破别有用心(biéyǒuyòngxīn)的人对他(tā)失踪(shīzōng)原因的各种荒诞猜测。
但是,第四次搜寻(sōuxún)仍然无功而返。
在第四次大规模搜寻结束后,国务院批准了中国科学院对彭加木善后处理的(de)安排:在彭加木失踪的库木库都克建立一个(yígè)永久性的标志;授予他革命(gémìng)烈士称号;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隆重举行彭加木追悼会。
55岁的(de)彭加木就这样永远消失在罗布荒原,成为了墓碑上的一个(yígè)名字。
此后数年,坊间(fāngjiān)一再流出关于他失踪的(de)各种传闻,甚至曾有人(rén)怀疑彭加木是因找水跟队友起了争执,被人杀害。作为考察队的副队长,夏训诚虽然没有亲见失踪事件的发生,但他觉得这种猜测实在太过恶毒(èdú)。
他认为,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的原因,最大的可能性有两种。
其一,彭加木只身外出后(hòu)迷路,被流沙掩埋。根据当时的天气(tiānqì)记录,6月16日晚到17日上午,当地刮了一场8-10级(jí)的大风,黄沙滚动,天昏地暗。
其二,彭加木在雅丹(yǎdān)土包(tǔbāo)阴面休息时,被坍塌的(de)松土掩埋。在库木库都克附近地区,分布着数百个大小不等、高低不一的雅丹土包,这些雅丹土包由比较坚硬的黏土层和疏松的细沙层构成,一刮大风,沙层极易坍塌,把(bǎ)人埋到底下。
但这也仅仅是推测而已(éryǐ)。从彭加木失踪一直到今天,人们其实(qíshí)从未停止对他(tā)的寻找,不断有人在罗布沙漠中找到疑似彭加木的“干尸”,但是至今,没有任何一具能够确定是彭加木本人。
几十年间,人们一遍一遍用红色(hóngsè)的油漆,重新填涂他纪念碑上被风沙腐蚀掉色的碑文。人们永远不会忘记,彭加木曾用(céngyòng)生命开启(kāiqǐ)了中国科学界对神秘罗布泊的探寻。
彭加木带领考察队进行的那次成功的考察,为后来的第二、第三次综合考察打下了(le)(le)重要基础,中国科学家终于逐渐夺回(duóhuí)了罗布泊研究的发言权,改变了“罗布泊研究在国外”的被动局面。此外,根据(gēnjù)他当年提出(tíchū)的关于钾盐的观点,数十年后,中国科学家经过大量努力,果然在罗布泊发现了超大型钾盐矿床,查明的钾盐储量超过(chāoguò)了2.5亿吨,彻底摘掉了中国“无钾”的帽子。
直至(zhízhì)今日,彭加木仍旧身埋在(zài)茫茫沙海里。罗布荒原可以掩埋一个人的身体,却无法掩埋他带给人们的感动和(hé)激励:那种一往无前、不惧牺牲的科学精神,永远是指引人类文明进步的力量。
本文首发于(yú)《北京日报》2017年3月7日
原标题:沙海迷途——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之谜
来源:北京日报纪事微信(wēixìn)公众号
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地纪念碑前的纪念。
1980年10月11日(rì),香港《中报》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载了一则奇闻(qíwén)。
文中称,当年9月14日下午7时许,一个名叫周光磊(zhōuguānglěi)的“中国(zhōngguó)留美学者”和几名朋友在(zài)华盛顿的一家饭馆吃饭的时候,竟然看见了在罗布泊失踪半年之久的著名科学家——彭加木。
这篇写得有鼻子有眼的(de)“奇闻”立刻引起海内外一片哗然。为了澄清事实,新华社记者专门(zhuānmén)就此事进行了调查,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明确(míngquè)表示,她和彭加木从来就不认识周光磊这个人。
新华社记者的调查(diàochá)虽然揭穿了所谓“周光磊”编造的谎言,但关于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的原因,一时间出现了很多以讹传讹的坊间版本。
当时流传最广的,是说彭加木从罗布泊秘密逃亡美国(měiguó)或者苏联。
在夏训诚看来,这样的(de)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,“营地附近都(dōu)有军事雷达,怎么可能美国或者(huòzhě)苏联的飞机把他接走,我们的部队能不发现?”
在《追寻彭加木》一书中,叶永烈回忆,当年年底由国家组织的第四次对彭加木的搜寻(sōuxún),在某种意义上也有澄清流言的目的,如果能够找到彭加木的遗体,就能够击破别有用心(biéyǒuyòngxīn)的人对他(tā)失踪(shīzōng)原因的各种荒诞猜测。
但是,第四次搜寻(sōuxún)仍然无功而返。
在第四次大规模搜寻结束后,国务院批准了中国科学院对彭加木善后处理的(de)安排:在彭加木失踪的库木库都克建立一个(yígè)永久性的标志;授予他革命(gémìng)烈士称号;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隆重举行彭加木追悼会。
55岁的(de)彭加木就这样永远消失在罗布荒原,成为了墓碑上的一个(yígè)名字。
此后数年,坊间(fāngjiān)一再流出关于他失踪的(de)各种传闻,甚至曾有人(rén)怀疑彭加木是因找水跟队友起了争执,被人杀害。作为考察队的副队长,夏训诚虽然没有亲见失踪事件的发生,但他觉得这种猜测实在太过恶毒(èdú)。
他认为,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的原因,最大的可能性有两种。
其一,彭加木只身外出后(hòu)迷路,被流沙掩埋。根据当时的天气(tiānqì)记录,6月16日晚到17日上午,当地刮了一场8-10级(jí)的大风,黄沙滚动,天昏地暗。
其二,彭加木在雅丹(yǎdān)土包(tǔbāo)阴面休息时,被坍塌的(de)松土掩埋。在库木库都克附近地区,分布着数百个大小不等、高低不一的雅丹土包,这些雅丹土包由比较坚硬的黏土层和疏松的细沙层构成,一刮大风,沙层极易坍塌,把(bǎ)人埋到底下。
但这也仅仅是推测而已(éryǐ)。从彭加木失踪一直到今天,人们其实(qíshí)从未停止对他(tā)的寻找,不断有人在罗布沙漠中找到疑似彭加木的“干尸”,但是至今,没有任何一具能够确定是彭加木本人。
几十年间,人们一遍一遍用红色(hóngsè)的油漆,重新填涂他纪念碑上被风沙腐蚀掉色的碑文。人们永远不会忘记,彭加木曾用(céngyòng)生命开启(kāiqǐ)了中国科学界对神秘罗布泊的探寻。
彭加木带领考察队进行的那次成功的考察,为后来的第二、第三次综合考察打下了(le)(le)重要基础,中国科学家终于逐渐夺回(duóhuí)了罗布泊研究的发言权,改变了“罗布泊研究在国外”的被动局面。此外,根据(gēnjù)他当年提出(tíchū)的关于钾盐的观点,数十年后,中国科学家经过大量努力,果然在罗布泊发现了超大型钾盐矿床,查明的钾盐储量超过(chāoguò)了2.5亿吨,彻底摘掉了中国“无钾”的帽子。
直至(zhízhì)今日,彭加木仍旧身埋在(zài)茫茫沙海里。罗布荒原可以掩埋一个人的身体,却无法掩埋他带给人们的感动和(hé)激励:那种一往无前、不惧牺牲的科学精神,永远是指引人类文明进步的力量。
本文首发于(yú)《北京日报》2017年3月7日
原标题:沙海迷途——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之谜
来源:北京日报纪事微信(wēixìn)公众号
1980年6月17日,中国著名(zhùmíng)科学家彭加木在新疆罗布泊进行科学考察(kēxuékǎochá)时神秘失踪,留下了一张(yīzhāng)简短的字条:“我往东去找水井。彭。6月17日,10点30分。”自此,他再也没有出现过。
时至今日,过去的四十多年里(lǐ),关于彭加木失踪的原因仍然众说纷纭(zhòngshuōfēnyún)。
被称为“死亡之海”的罗布泊(luóbùpō),是荒漠中的荒漠,是曾被列为军事禁区的核试验场,是埋藏(máicáng)着楼兰古城的历史宝库,也是无数探险家和(hé)科考工作者心中的圣地。
45年前,著名科学家彭加木(péngjiāmù)就是在罗布泊考察(kǎochá)时不幸失踪,永远地消失在那片沙海中。
彭加木(péngjiāmù)在罗布泊失踪的(de)(de)消息震惊了1980年的中国(zhōngguó),国家曾组织了前后4次大规模的寻找,却始终没发现他的任何踪影。在此后的若干年里,许多敬仰彭加木的民间人士自发组织探险队,到罗布泊寻找彭加木,也都以无果告终。
彭加木的(de)失踪(shīzōng)成为20世纪(shìjì)世界科学界之谜,三十多年间,许多当年的亲历者都曾回忆过他失踪前后的事情,坊间也传出许多关于他失踪经过的版本。然而时至今日(shízhìjīnrì),彭加木的遗体没有找到,他的失踪之谜也没有解开。
 彭加木(左)在新疆(xīnjiāng)考察时留影。
1980年6月(yuè)24日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里传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:著名科学家彭加木(péngjiāmù)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。
此时,距离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已经是第7天了。
也是在那一天,原中(zhōng)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(shāmò)研究所所长、时任罗布泊科学考察队副队长的夏训诚,在从北京返回乌鲁木齐的火车车厢中,听到了这个令他无法相信(xiāngxìn)的广播。
2017年记者采访夏训诚时,他已经83岁了。在北京的家中,当他回忆起当时(dāngshí)的情景,仍唏嘘(xīxū)不已。
“当时全车厢的人都(dōu)一下子安静了,我更是不敢相信,彭加木(péngjiāmù)是我的战友和同事,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,赶快赶回去,到现场(xiànchǎng)去找他,救他。”夏训诚说。
事实上,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当时本该和彭加木在一起(yìqǐ)。他们一起筹备了赴罗布泊的(de)科学考察(kǎochá)队,并制定了三期考察计划,夏训诚任副队长,彭加木任队长。但是就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,夏训诚突然接到了中国科学院的通知,让他参加考察团,赴美国进行沙漠考察。
在征求彭加木意见(yìjiàn)时,彭加木态度鲜明地劝说夏训诚赴美考察,不能失去难得的好机会(jīhuì)。“他还说,从长远看,这次(zhècì)进入罗布泊(luóbùpō)的项目考察,关键性的专业考察是在来年的第二次和第三次。”夏训诚回忆道,彭加木随信寄给他一百多张此前中国考察队在罗布泊拍摄的幻灯片(huàndēngpiàn),他建议夏训诚把这些照片带到美国去,并告诉全世界: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已经踏上(tàshàng)了罗布泊这块世界瞩目的神秘之地。
这些照片确实在(zài)当年的美国科学界引起了巨大轰动,然而让夏训诚万万没有(méiyǒu)想到的是,仅仅一个多月后,彭加木永远消失在罗布泊,再也不能兑现和他的科考(kēkǎo)之约了。
1980年的中国(zhōngguó),新闻传播还只限于报纸和广播,电视都尚未普及,发出第一篇关于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新闻报道的人,是(shì)新华社驻新疆分社记者赵全章。
1980年6月20日,赵全章到乌鲁木齐机场送人(sòngrén),新疆(xīnjiāng)八一农学院的副教授徐鹏告诉他(tā),自己无意间从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得知,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了。
这样的信息在(zài)当时是(shì)要严格保密的。出于记者的新闻敏感,赵全章在归途中,特地在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门口下了车(chē)。他在新疆分院值班室核实(héshí)了彭加木失踪的情况,写出了关于此事的第一篇新闻稿,但只是作为新华社内参报到了北京,并未准备公开发表。
由于是供领导看的内参,这篇新闻稿中提出搜索彭加木工作中的困难:只有一两架(liǎngjià)飞机,地面搜索人员也(yě)很(hěn)不够,意在呼吁加大搜索力量。
翌日——6月21日,新华社社长穆青看了内参上(shàng)这一新闻,当即决定:发公开稿(gǎo)。
经过中央领导批示后,新华社新疆分社(fēnshè)在6月23日晚上(wǎnshàng),发出了关于彭加木失踪的(de)第一条电讯。在此之前,中科院上海分院已经提前去看望了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,让她心里有所准备。
第二天,全国(quánguó)的媒体(méitǐ)都铺天盖地地以各种形式播发了这条新闻: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(yuànzhǎng)、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进入罗布泊地区进行科学考察的时候,不幸失踪。
消息一出,举(jǔ)国震惊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数次寻找的毫无结果,彭加木失踪成了当时全国最(zuì)牵动人心的事情。在彭加木失踪之处,附近的居民自发组织起寻人的队伍;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信雪片(xuěpiàn)般地飞向新疆,一时间,彭加木成为(chéngwéi)了家喻户晓(jiāyùhùxiǎo)的人物,许多人为他的事迹所感动和激励。
然而,彭加木并不是第一个在罗布泊倒下(dǎoxià)的人,也不是最后一个。
在过去的100多年间,罗布泊一直被视为一片神秘的土地。从19世纪末(shìjìmò)开始,这里就曾吸引一批又一批中外探险家千山万水地来到此地,探究这片沙漠深处的秘密。死亡的威胁,也不曾(bùcéng)挡住人们走近它(tā)的脚步。在彭加木失踪16年后,即将完成徒步穿越新疆罗布泊全境壮举的探险家余纯顺,在一场突然而(ér)至的沙暴中不幸遇难(bùxìngyùnàn)。
这片极具危险(wēixiǎn)的“死亡之海”,为何具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?
1964年(nián)10月16日,中国成功试验了一颗原子弹,随着惊天动地的(de)巨响,一朵巨大的蘑菇云从中国第一个(dìyígè)核试验基地——马兰基地升腾而起。
马兰基地所在(suǒzài)的位置(wèizhì),正是人迹罕至的罗布泊沙漠。罗布泊最广为人知的原因,就是因为这片荒漠曾被作为核试验场。
其实,漫长的历史中,罗布泊并非一直如此干旱和荒凉。从它(tā)名字中的“泊”就能看出,这里曾经是(shì)个水源丰沛之地。
在中国的(de)史料典籍中,罗布泊曾有(yǒu)过许多名称:有的因它(tā)的特点而命名,如泑泽、盐泽、涸海等;有的因它的位置而得名,如蒲昌海、牢兰海、孔雀海、洛普池等。元代以后,此地被称为罗布淖尔。
罗布淖尔系蒙古语音译名,意为(yìwèi)多水汇集之湖。罗布泊(luóbùpō)位于塔里木盆地的最低处,海拔780公尺,塔里木河、孔雀河、车尔臣河、疏勒河等汇集于此(cǐ),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咸水湖。
在历史上,罗布泊(luóbùpō)的最大(dà)面积为5350平方公里,曾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湖,面积仅次于青海湖。
水量丰沛的罗布泊“广袤三百里,其水亭居,冬夏不增减”,可见(kějiàn)它当时的丰盈,古人甚至(shènzhì)曾误认为罗布泊为黄河的上源,这种(zhèzhǒng)说法从先秦至清末,流传了2000多年。
直到20世纪(shìjì)中后期,塔里木河流量减少,罗布泊周围沙漠化严重。20世纪70年代(niándài)末,罗布泊完全干涸。
1972年7月,从美国宇航局发射的地球资源卫星拍摄(pāishè)的照片上,人类第一次看到了罗布泊的全貌(quánmào)。
照片(zhàopiān)中干涸的罗布泊竟酷似人的一只耳朵,不但有耳轮(ěrlún)、耳孔,甚至还有耳垂。罗布泊因此被誉为“地球之耳”。事实上,这种奇特的地貌是湖水(húshuǐ)迅速退缩而形成的。
彭加木(左)在新疆(xīnjiāng)考察时留影。
1980年6月(yuè)24日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里传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:著名科学家彭加木(péngjiāmù)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。
此时,距离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已经是第7天了。
也是在那一天,原中(zhōng)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(shāmò)研究所所长、时任罗布泊科学考察队副队长的夏训诚,在从北京返回乌鲁木齐的火车车厢中,听到了这个令他无法相信(xiāngxìn)的广播。
2017年记者采访夏训诚时,他已经83岁了。在北京的家中,当他回忆起当时(dāngshí)的情景,仍唏嘘(xīxū)不已。
“当时全车厢的人都(dōu)一下子安静了,我更是不敢相信,彭加木(péngjiāmù)是我的战友和同事,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,赶快赶回去,到现场(xiànchǎng)去找他,救他。”夏训诚说。
事实上,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当时本该和彭加木在一起(yìqǐ)。他们一起筹备了赴罗布泊的(de)科学考察(kǎochá)队,并制定了三期考察计划,夏训诚任副队长,彭加木任队长。但是就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,夏训诚突然接到了中国科学院的通知,让他参加考察团,赴美国进行沙漠考察。
在征求彭加木意见(yìjiàn)时,彭加木态度鲜明地劝说夏训诚赴美考察,不能失去难得的好机会(jīhuì)。“他还说,从长远看,这次(zhècì)进入罗布泊(luóbùpō)的项目考察,关键性的专业考察是在来年的第二次和第三次。”夏训诚回忆道,彭加木随信寄给他一百多张此前中国考察队在罗布泊拍摄的幻灯片(huàndēngpiàn),他建议夏训诚把这些照片带到美国去,并告诉全世界: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已经踏上(tàshàng)了罗布泊这块世界瞩目的神秘之地。
这些照片确实在(zài)当年的美国科学界引起了巨大轰动,然而让夏训诚万万没有(méiyǒu)想到的是,仅仅一个多月后,彭加木永远消失在罗布泊,再也不能兑现和他的科考(kēkǎo)之约了。
1980年的中国(zhōngguó),新闻传播还只限于报纸和广播,电视都尚未普及,发出第一篇关于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新闻报道的人,是(shì)新华社驻新疆分社记者赵全章。
1980年6月20日,赵全章到乌鲁木齐机场送人(sòngrén),新疆(xīnjiāng)八一农学院的副教授徐鹏告诉他(tā),自己无意间从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得知,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了。
这样的信息在(zài)当时是(shì)要严格保密的。出于记者的新闻敏感,赵全章在归途中,特地在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门口下了车(chē)。他在新疆分院值班室核实(héshí)了彭加木失踪的情况,写出了关于此事的第一篇新闻稿,但只是作为新华社内参报到了北京,并未准备公开发表。
由于是供领导看的内参,这篇新闻稿中提出搜索彭加木工作中的困难:只有一两架(liǎngjià)飞机,地面搜索人员也(yě)很(hěn)不够,意在呼吁加大搜索力量。
翌日——6月21日,新华社社长穆青看了内参上(shàng)这一新闻,当即决定:发公开稿(gǎo)。
经过中央领导批示后,新华社新疆分社(fēnshè)在6月23日晚上(wǎnshàng),发出了关于彭加木失踪的(de)第一条电讯。在此之前,中科院上海分院已经提前去看望了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,让她心里有所准备。
第二天,全国(quánguó)的媒体(méitǐ)都铺天盖地地以各种形式播发了这条新闻: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(yuànzhǎng)、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进入罗布泊地区进行科学考察的时候,不幸失踪。
消息一出,举(jǔ)国震惊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数次寻找的毫无结果,彭加木失踪成了当时全国最(zuì)牵动人心的事情。在彭加木失踪之处,附近的居民自发组织起寻人的队伍;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信雪片(xuěpiàn)般地飞向新疆,一时间,彭加木成为(chéngwéi)了家喻户晓(jiāyùhùxiǎo)的人物,许多人为他的事迹所感动和激励。
然而,彭加木并不是第一个在罗布泊倒下(dǎoxià)的人,也不是最后一个。
在过去的100多年间,罗布泊一直被视为一片神秘的土地。从19世纪末(shìjìmò)开始,这里就曾吸引一批又一批中外探险家千山万水地来到此地,探究这片沙漠深处的秘密。死亡的威胁,也不曾(bùcéng)挡住人们走近它(tā)的脚步。在彭加木失踪16年后,即将完成徒步穿越新疆罗布泊全境壮举的探险家余纯顺,在一场突然而(ér)至的沙暴中不幸遇难(bùxìngyùnàn)。
这片极具危险(wēixiǎn)的“死亡之海”,为何具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?
1964年(nián)10月16日,中国成功试验了一颗原子弹,随着惊天动地的(de)巨响,一朵巨大的蘑菇云从中国第一个(dìyígè)核试验基地——马兰基地升腾而起。
马兰基地所在(suǒzài)的位置(wèizhì),正是人迹罕至的罗布泊沙漠。罗布泊最广为人知的原因,就是因为这片荒漠曾被作为核试验场。
其实,漫长的历史中,罗布泊并非一直如此干旱和荒凉。从它(tā)名字中的“泊”就能看出,这里曾经是(shì)个水源丰沛之地。
在中国的(de)史料典籍中,罗布泊曾有(yǒu)过许多名称:有的因它(tā)的特点而命名,如泑泽、盐泽、涸海等;有的因它的位置而得名,如蒲昌海、牢兰海、孔雀海、洛普池等。元代以后,此地被称为罗布淖尔。
罗布淖尔系蒙古语音译名,意为(yìwèi)多水汇集之湖。罗布泊(luóbùpō)位于塔里木盆地的最低处,海拔780公尺,塔里木河、孔雀河、车尔臣河、疏勒河等汇集于此(cǐ),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咸水湖。
在历史上,罗布泊(luóbùpō)的最大(dà)面积为5350平方公里,曾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湖,面积仅次于青海湖。
水量丰沛的罗布泊“广袤三百里,其水亭居,冬夏不增减”,可见(kějiàn)它当时的丰盈,古人甚至(shènzhì)曾误认为罗布泊为黄河的上源,这种(zhèzhǒng)说法从先秦至清末,流传了2000多年。
直到20世纪(shìjì)中后期,塔里木河流量减少,罗布泊周围沙漠化严重。20世纪70年代(niándài)末,罗布泊完全干涸。
1972年7月,从美国宇航局发射的地球资源卫星拍摄(pāishè)的照片上,人类第一次看到了罗布泊的全貌(quánmào)。
照片(zhàopiān)中干涸的罗布泊竟酷似人的一只耳朵,不但有耳轮(ěrlún)、耳孔,甚至还有耳垂。罗布泊因此被誉为“地球之耳”。事实上,这种奇特的地貌是湖水(húshuǐ)迅速退缩而形成的。
 卫星(wèixīng)拍下的“地球之耳”罗布泊。
罗布泊的(de)神秘之处,并不仅仅在于它奇特(qítè)的地理构造,更源于它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湮灭在漫漫黄沙下的历史传说。
罗布泊历史上最繁华的一个时期,是在“楼兰(lóulán)王国”兴盛之时。楼兰古城地处罗布泊的西北侧,这里曾经(céngjīng)是丝绸之路南支的咽喉门户。
楼兰于公元前176年以前(yǐqián)建国、公元630年消亡,历时800多年。随着(suízhe)楼兰国的消亡,这里渐渐成为人迹罕至之地,丝绸之路的故道不复存在,罗布荒原逐渐被人们所遗忘(yíwàng)。
直到1900年3月,瑞典探险家斯文(sīwén)·赫定探险队沿着干枯的孔雀河左河床来到罗布荒原,意外(yìwài)地发现了隐藏在历史(lìshǐ)沙砾中一千多年的楼兰古城,这一“神迹”才重现于世。
斯文·赫定回到欧洲,向全世界公布了罗布荒原上的(de)“沙埋文明”,轰动一时。神秘的“楼兰(lóulán)”是(shì)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成就之一,而楼兰古国所在(suǒzài)的这一片罗布荒原,成为了世界探险家趋之若鹜的神秘地带。
斯文·赫定曾在他那部著名的《亚洲腹地探险8年》一书中写道:“罗布泊使我惊讶,它像座仙湖(xiānhú),水面像镜子一样,在和煦的阳光(yángguāng)下,我乘舟而行,如(rú)神仙一般。”
作为此地最大的(de)沙漠咸湖,罗布泊也因此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。
上世纪初叶,罗布泊的“游移之谜(zhīmí)”曾引起世界学术界的极大争论。
最早(zuìzǎo)到新疆(xīnjiāng)考察的中外科学家们曾对罗布泊(luóbùpō)的确切位置争论不休,斯文·赫定认为罗布泊存在南北湖区,由于(yóuyú)入湖河水带有大量泥沙,沉积后抬高了湖底,原来的湖水就自然向另一处更低的地方流去,又过许多年,抬高的湖底会由于风蚀再次降低,湖水再度回流,这个周期为1510年,所以(suǒyǐ),他认为罗布泊是一个在沙漠中不断游移的湖。
斯文·赫定这(zhè)一学说,在(zài)当时曾得到(dédào)了世界普遍认可。“游移之谜”给罗布泊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,这片幽灵般的湖泊,再一次引起了全世界探险家的极大兴趣。
1927年,中国科学家第一次靠近(kàojìn)了这片“幽灵湖泊”。斯文·赫定在筹备第六次中亚考察时,决定由中瑞两国共同(gòngtóng)组成一个(yígè)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。时任北京大学教务长的知名学者徐炳旭(xúbǐngxù)担任中方团长,团中尽数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专家,如地质与古生物学家丁道衡、考古学家黄文弼、地理学家(dìlǐxuéjiā)陈宗器等。
这次考察从1927年持续到1933年,考察队先后在罗布泊、吐鲁番和塔里木盆地(tǎlǐmùpéndì)进行考古调查(diàochá)和部分试掘,撰写了《罗布淖尔考古记(jì)》、《吐鲁番考古记》、《塔里木盆地考古记》等,在国内出版,引起很大反响(fǎnxiǎng)。
此后的(de)很长一段时间,罗布泊的研究湮灭于连年战火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9年,罗布荒原终于又(yòu)迎来了一支新的科学考察队。
从1956年到1959年,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(zōnghé)考察队对塔里木下游和罗布泊地区(dìqū)进行了新中国成立后最大规模的一次综合考察,当时,队员们是乘着舟进入(jìnrù)罗布泊的。
夏训诚因被分在北疆(běijiāng)组考察,遗憾地与当时(dāngshí)尚未干涸的(de)罗布泊失之交臂。他说,那次考察留下了人类在罗布泊荡舟的最后记录,“由于1952年在拉依河筑坝,使塔里木河和孔雀河(kǒngquèhé)彻底分流,孔雀河下泄的河水逐渐断绝,罗布泊在上世纪(shìjì)70年代初全部干涸了,终结了它作为一个湖泊的历史。”
那次考察后不久,罗布泊被定为核试验场,从此成为军事禁区。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,任何与核试验无关的人都不得进入(jìnrù)这个地区(dìqū)。
彭加木也没有参加(cānjiā)那次考察。那时他正在上海(shànghǎi)的医院中,与恶性肿瘤、癌细胞搏斗着。
“彭加木”这个名字,也刚刚出现(chūxiàn)不久。
1947年,22岁的广东番禺青年彭家睦从中央大学(1949年更名(gēngmíng)南京大学)农学院毕业,到(dào)北京大学农学院任教,专攻农业化学。1949年,他被分配(fēnpèi)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。
1956年初,中央发出了“向(xiàng)科学进军”的号召,正当(zhèngdāng)此时,彭家睦迎来了一个对他个人发展千载难逢的机会。
科学院的领导研究决定,派年轻的彭家睦到莫斯科(mòsīkē)去(qù)学习一项新的技术——核磁共振,办理完出国手续即刻便要动身。
能够去苏联学习,无疑是一个好机会,彭家睦自然是高兴极了,但是他(tā)马上又(yòu)陷入了两难的选择中。
就在这个当口,中国科学院为了开发祖国边疆的丰富资源,组织了综合考察委员会。这个委员会此时正在“招兵买马(zhāobīngmǎimǎ)”,吸收各方面(fāngmiàn)科技人才,准备(zhǔnbèi)组成若干小组,分赴祖国边疆各地进行实地考察。
究竟是去国外留学还是去边疆考察,31岁的彭家(péngjiā)睦面临重要的人生选择,经过反复(fǎnfù)考虑后,他选择了后者。
彭家睦曾经亲笔写下作出这一选择的(de)(de)原因:“我必须在出国和到边疆之间立刻做出选择,我考虑的结果,认为出国学习的任务虽然重要,但可以由别的同志来完成,别的同志也乐于去(qù)干(gàn),为了让科学在祖国遍地开花,作为一个共产党员,应当选择到最艰苦的地方去。”
在同样(tóngyàng)毕业于南京大学的(de)夏训诚看来,彭家睦当年的选择着实令人敬佩:“上海的科研条件自然(zìrán)比边疆要好得多,而且他当时在植物学领域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,但是为了边疆的科研,他甘愿(gānyuàn)做铺路石子。”
1956年3月, 彭家睦的申请正式得到了批准,他如愿以偿地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(shēngwùhuàxué)研究所调到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工作(gōngzuò),当时的职务是助理(zhùlǐ)研究员。
此时,他的户口也从上海迁到了北京(běijīng)。在(zài)迁户口时,彭家睦打(dǎ)了一个改名报告,把“彭家睦”改为了“彭加木”。从此,他一直用“彭加木”这个名字。
实际上,在迁户口之前,他就已经在使用“彭加木”的名字了。为了争取参加中(zhōng)国边疆科考,彭加木直接写信给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。他在信中(xìnzhōng)写道:“我具有从荒野中踏出一条(yītiáo)道路(dàolù)的勇气。”在信的末尾,署名并不是“彭家睦”,而是“彭加木”。
从“彭家睦”到“彭加木”,其实是他表示“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”的决心。彭加木认为“家睦”只是希望家庭和睦,着眼于(zhuóyǎnyú)小家(xiǎojiā),太狭隘(xiáài)了;他要跳出小家庭,为边疆“添草加木”。
那一年的秋天,彭加木第一次来到(láidào)乌鲁木齐。当时(dāngshí)新疆的科研事业只是有了一点点萌芽,而在生物化学研究方面几乎是一个空白。一到新疆,彭加木就帮助当地筹建了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。然而(ránér),这个豪情万丈的垦荒者,却突然遭受了一个重大打击(dǎjī)。
1957年初,彭加木突然被查出患有纵隔障恶性肿瘤,返回上海治疗。以当时的医疗条件,医生们根据(gēnjù)有限的医学文献和病例判断(pànduàn),彭加木最多只能(zhǐnéng)活两年。
祸不单行的是,在住院期间,彭加木又(yòu)被查出还患有另一种恶性肿瘤——网状细胞(xìbāo)淋巴瘤,患这种病一般只能活几个月。
等于是被判了死刑的彭加木却没有(méiyǒu)被病魔打倒(dǎdǎo),一年以后,他竟然奇迹般地康复了。虽然医生严令禁止他离开上海(shànghǎi),但是彭加木刚一出院就接二连三地要求“放虎归山”,回到新疆去工作。
1958年的春天,一个险些被癌症夺去生命的人,又踏上了西行(xīxíng)的旅程,彭加木与罗布泊也从此正式(zhèngshì)结缘。
彭加木在新疆工作期间,一共有过四次对(duì)新疆地区的大规模考察(kǎochá)。这些考察包括人文、地理、生物、矿产资源、文物古籍、风土民情等。
1959年,彭加木(péngjiāmù)曾到过罗布泊北部地区,采集过土壤标本。经过化验,他发现此地土壤中的(de)钾含量(hánliàng)非常高。1964年,他对流入罗布泊的孔雀河、塔里木河、车尔臣河等河流进行了综合考察。参与这次考察的共有四个人(rén),由彭加木带队(dàiduì),此外还有新疆化学所的两名科研工作者和一名司机。考察从9月上旬到10月下旬,历时40多天,行程近5000公里(gōnglǐ)。
在(zài)对流入罗布泊的(de)几条河的钾含量作了初步分析后,彭加木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——罗布泊极有可能蕴藏巨大储量的钾盐。
钾盐是农用钾肥的生产原料,在我国属大宗紧缺(jǐnquē)矿种,中国(zhōngguó)境内可溶性钾盐资源严重不足,需要大量进口。
彭加木同时判断,在罗布泊的(de)盐层中,还含有宝贵的原料,比如制造(zhìzào)飞机所需的镁,稀有金属锂(lǐ)等。另外,那里还可能有重水资源。重水是重要的中子减速器,无论是建造原子能反应堆还是制造原子弹都会用到它(tā),此外,它还是制造氢弹的原料,属于重要的战略资源。
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,我国(wǒguó)在钾盐勘查方面投入(tóurù)大量(dàliàng)的人力和经费,除了在柴达木盆地取得重大突破外,其它(qítā)地区成果甚微,以致出现了中国“无钾论”的看法。中国是否能再找到大型钾盐矿床,一直是科学界关注的焦点。
那次考察中,在塔里木河下游,彭加木发现河水(héshuǐ)的(de)钾含量在逐渐增加。他根据气象资料推算出河水的流量,并从河水的流量数据(shùjù)推算出河流搬运钾元素的大约值,由此(yóucǐ)估算出罗布泊每年会积聚约75万吨钾,可能还含有其他稀有金属和重水等资源。
夏训诚说,彭加木是(shì)第一个提出罗布泊有钾盐矿(kuàng)的(de)人。如果罗布泊果真富集钾盐矿,这里就不再是人迹罕至的荒漠,而是一个巨大的“聚宝盆”。
在新疆进行这一次考察时,彭加木39岁,在罗布泊寻找钾盐矿成为了他对这片神秘(shénmì)区域最初的研究目标。遗憾(yíhàn)的是,由于“文革”的影响,他对罗布泊的研究计划(jìhuà)也不得不搁浅了十余年。
“地球之耳”的(de)神秘大门对彭加木再次打开的时候,他已经54岁了(le)。对一个科学家来说,这个年龄还(hái)算年轻。然而,重新走进这道大门仅仅一年时间,彭加木的生命戛然而止。
1979年的(de)冬天,刚刚率领科学考察队从(cóng)天山最高峰——托木尔峰归来的夏训诚,突然接到新疆考古所副所长穆舜英打来的电话。
穆舜英在电话中说,由中日联合组成的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即将(jíjiāng)来新疆,在罗布泊(luóbùpō)附近进行(jìnxíng)实地拍摄。夏训诚被聘请为“顾问”,要组成一个“先遣队”进入罗布泊打个前站。
罗布泊在上世纪60年代(niándài)被列为军事禁区,又因“文革”的关系,此地的科学考察一直处于停滞状态。对夏(duìxià)训诚来说,能够再次进入罗布泊就像是“圆梦”一样,兴奋之余,他突然想到(xiǎngdào)了老朋友彭加木。
致力于沙漠治理的夏训诚从上(shàng)世纪50年代起就一直在新疆进行考察和研究,因工作关系与彭加木(péngjiāmù)结识多年,“我知道他一直想去罗布泊找钾盐,这个机会千载难逢(qiānzǎinánféng)。”夏训诚说。
于是,他(tā)把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告诉了(le)彭加木,彭加木当时竟高兴得跳了起来,连说“太好了(tàihǎole)”。夏训诚现在仍然记得,彭加木当时像孩子一样握着他的手,一直恳求他帮忙,与有关单位(dānwèi)联系参加这次考察。
夏训诚回忆,当时联系的过程颇为复杂,罗布泊毕竟是几十年的军事禁区。“据我了解,《丝绸之路(sīchóuzhīlù)》摄制组此行进入(jìnrù)罗布泊,是邓小平(dèngxiǎopíng)同志亲自(qīnzì)批准的。”最终,执着的彭加木还是得到了这次进入罗布泊的机会。
“先遣队”不是一个(yígè)严格(yángé)的科学考察的组织,但是每(měi)一个队员都有自己心里的“小算盘”,作为地理工作者,夏训诚关注罗布泊的自然环境变迁情况;而对于彭加木来说,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延续上世纪60年代未完成的考察计划,在罗布泊寻找钾盐(jiǎyán)。
这是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,罗布泊(luóbùpō)地(dì)区第一次向非军事人员开放。20余天的时间(shíjiān)里,6辆吉普车组成的车队穿过了沉寂的荒原,穿过楼兰古城和白龙堆雅丹,在完成了几次横向与纵向穿插罗布泊西部的考察后,“先遣队”成功地回到了乌鲁木齐的基地(jīdì)。
在离开基地的前一天(qiányītiān),彭加木向夏训诚提议,由他俩(tāliǎ)牵头,上书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建议正式组建考察队,对罗布泊进行(jìnxíng)全面的综合考察。
彭加木此时提出考察计划,已(yǐ)不仅仅(bùjǐnjǐn)为了他寻找已久的钾盐矿。一个多世纪以来(yǐlái),俄国人、瑞典人、日本人一次一次来到罗布泊(luóbùpō)考察、探险,写出了许多关于罗布泊的文章,以至于国外竟有一种言论:“罗布泊在中国,而罗布泊的研究在外国”。彭加木向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表示,要夺回中国科学家在罗布泊的发言权。
几天以后,彭加木正式调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,这无疑对(duì)组建罗布泊考察队起到了积极的(de)作用。
1980年初(niánchū),通过各方面的努力,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(fēnyuàn)正式下达了成立(chénglì)罗布泊科学考察队的文件,并决定由彭加木担任队长,夏训诚担任副队长。
彭加木心中多年的夙愿,即将(jíjiāng)达成。
根据计划(jìhuà),这次对罗布泊的综合考察分三次进行。1980年的第一次考察主要(zhǔyào)是路线考察,时间定在1980年的5、6月间,第二年再进行后两次(liǎngcì)考察。
“第一次考察之所以(zhīsuǒyǐ)定在(zài)这个月份,是因为这时正是沙漠荒原风沙季节和酷热季节的‘空档’。”夏训诚说。但是他认为当时的计划并(bìng)不周全,“我们当时不知道,实际上罗布泊地区(dìqū)并没有这种‘空档’,或者说很短促。”
在制定计划的同时,考察队正式开始“招兵买马”。夏训诚主持组建队伍的工作,他从新疆分院的好几个部门抽调了6名专业(zhuānyè)人员和3名司机、一名后勤(hòuqín),这十位同志组成(zǔchéng)了一支罗布泊科学考察队。
5月3日,由彭加木率队,罗布泊(luóbùpō)科学考察队从乌鲁木齐出发,正式向罗布泊进发了(le)。因为在出发前突然接到去美国考察的通知,夏训诚遗憾地(dì)错过了参加第一次路线考察的机会。
夏训诚直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,建议组建考察队时,彭加木曾悲愤地说(dìshuō):“我不希望在罗布泊全是外国人(wàiguórén)留下的足迹,作为一个中国人,我就觉得应该把自己的骨头(gútou)埋在罗布泊,使它的土壤多一点(duōyìdiǎn)中国的有机质!”
这不是一句玩笑,而是彭加木(péngjiāmù)的真实想法。如果说科学探索总(zǒng)需要牺牲,他是在进入罗布泊之前,就已经作好了牺牲准备的。
夏训诚万万没有想到,仅仅一个多月以后,彭加木的话(dehuà)一语成谶。
作为对罗布泊的(de)第一次深入性考察,彭加木的计划是十分大胆的。
他打算率队从北至南,纵穿(zòngchuān)罗布泊。在他看来,只有纵穿罗布泊,才能弄清这个神秘之地(zhīdì)的真实面目。
但是(dànshì),第一次纵穿并未成功。彭加木(péngjiāmù)在日记中写道:“我们在5月9日开始进入湖区,有(yǒu)一个七人(qīrén)探路小分队,自北往南纵贯罗布泊湖底。湖表面已没有水,有些地面松软陷车,有些地面则比较平整。汽车车胎由于锋利的盐晶块切割,损耗过大,无法继续前进。”
那天晚上,考察队只能原地宿营。因为当时(dāngshí)所带的汽油和水(shuǐ)都消耗了不少,彭加木只得决定原路返回,重新补充油、水之后再度前进。
湖底的(de)盐晶块是前进的极大阻碍,最终用来给考察队(kǎocháduì)开路的,竟然是队员们手中十几(shíjǐ)磅重的大铁锤。这个方法也是彭加木提出(tíchū)的,最初遭到队员们的一致反对,大家认为在罗布泊湖底用铁锤人工开路简直是天方夜谭。
事实证明(shìshízhèngmíng),彭加木的意见是正确的。5月30日,考察队重新出发,又一次到了这个地区,大家拿着铁锤下车,一锤一锤地把车轮前的盐晶块(yánjīngkuài)砸碎。汽车(qìchē)颠簸前行,直到他们找到了古河道的入湖口,路(lù)才一下子平顺了起来,盐晶块对车行的阻碍得以解除。
汽车沿着古河道走了两天,终于完成了纵贯罗布泊的计划。沿途(yántú),考察队进行了简单的地质勘探,彭加木凿开盐壳,从下面瓦蓝色(lánsè)的沙层中取出一个水样(shuǐyàng),兴奋地对大家说:“这里可能有‘重水’!”能够在地域广阔的罗布泊找到重水资源,这无疑(wúyí)是(shì)对中国核物理工业发展的一个巨大贡献。
彭加木曾这样评价此次纵穿罗布泊的(de)经历(jīnglì):“此次胜利的穿越盐壳地带,自北而南纵贯罗布泊干涸湖底(húdǐ)成功,是一个很大的收获,这是前所未有的,对罗布泊洼地中心区域已经有了一些了解,可算(kěsuàn)得是敲开了罗布泊的大门。”
考察队在6月5日到达(dàodá)了考察的最后一站——米兰农场。
进入米兰(mǐlán)农场(nóngchǎng)以后,考察队的队员们如同卸下了千斤重担。按原定的方案,在米兰农场休息几天后考察队就可以启程回乌鲁木齐了。
就在此时,彭加木突然向队员们提出了(le)“东进计划”。
这次考察原计划到7月3日结束,还有近一个月时间。彭加木建议(jiànyì)暂不回乌鲁木齐,利用剩下的这些时间一鼓作气(yīgǔzuòqì)完成对(duì)整个罗布泊地区的考察。
1979年冬天,彭加木作为纪录片《丝绸之路》的“先遣队”成员之一,曾完成了对罗布泊西部的考察(kǎochá),这次,考察队又从罗布泊的中部纵穿(zòngchuān)而过,他计划在余下一个月(yígèyuè)的时间里,沿罗布泊东部北上,穿过疏流河(liúhé)直至敦煌,完成对罗布泊地区的全面考察,最后再(zài)回乌鲁木齐。
虽然队员们已经非常疲惫,但最终大家还是(háishì)决定采纳彭加木的建议。
彭加木通过电报向中科院新疆分院(fēnyuàn)汇报请求批准。新疆分院接到电报后,经研究同意他们的计划,但(dàn)一再嘱咐(yīzàizhǔfù),一定要注意安全,有情况及时与基地联系。
在准备出发,装(zhuāng)汽油和水的时候,彭加木提议可以多装一桶汽油,少装一桶水。原因是从地图上看,到了库木库都克这个地方(dìfāng)有水井(shuǐjǐng),可以在这个地方补充水源。根据路程(lùchéng)计算,到库木库都克只有400多公里,最多两天即可赶到。
然而,在这一段路上,考察队(kǎocháduì)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麻烦。
6月11日,考察队一早从米兰出发,一直赶路到天黑。十几个小时,车子只走了(le)58公里(lǐ),还不到计划行程的(de)一半。一路都是松软的沙石地,三辆车不是这辆陷进了泥坑,就是那辆困(kùn)在了沙窝子,有时候几个小时才能把一辆车从泥坑里弄出来,此后的几天里也都是如此,结果,本来预计两天的路程考察队走了整整(zhěngzhěng)6天。
6月16日下午6时左右,考察队终于赶到(gǎndào)了库木库都克,此时大家都已是筋疲力尽,却不得不再次外出——由于行程(xíngchéng)被耽搁,出发时带的汽油和水此时都快要消耗(xiāohào)殆尽了。
“库木库都克”是维吾尔语(wéiwúěryǔ)“沙井”的意思。从考察队带的那张地图看,这里确实标有水井。考察队支好帐篷,休息了一会儿(yīhuìer),便立刻出发去找水(zhǎoshuǐ)。
让彭加木和队员们大为失望的是,从下午找到晚上,这片茫茫的沙漠中根本没有水(shuǐ)井的踪影。眼下,所剩的汽油只能供三辆(sānliàng)车行驶几十公里;水,则只剩下一汽油桶,且(qiě)已变质,难以饮用。
没有水和汽油,考察队员们即刻就面临生命危险,几乎陷入绝境的(de)考察队决定向部队紧急求助(qiúzhù)。
6月16日晚上10时10分,彭加木亲自起草了发给部队的告急电报:“我们已到(dào)达了库木库都克以西大约十公里。我们缺油和水(shuǐ),请求紧急(jǐnjí)支援油、水各500公斤,现有的水只能维持到18日。”
电报发出后(hòu),正在大家焦急等待回复的时候(shíhòu),彭加木提出了新的建议。
一向节俭的彭加木认为,用直升机运水(yùnshuǐ)太贵了(le)。直升机飞行一小时,在那个年代要花2000多块钱,从驻军基地到宿营地,来回(láihuí)要飞好几个小时。他建议大家自力更生,尽量自己找水。
不久前,他和别人闲聊中听说,年初的时候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曾经在“八一泉(quán)”加过(jiāguò)水。“八一泉”位于疏流河故道北岸,在库木库都克东北约30公里处(chù)。
所以,彭加木建议开车(kāichē)再(zài)往东面去找一次水井,但是这个建议遭到了(le)队员们的全体反对。大家计算了一下,这一路线要用掉(diào)大概半桶汽油,大家一致认为不能再消耗本已不多的汽油,应该等与部队联系上以后,再作打算。
第二天上午(shàngwǔ)11点半,考察队收到了部队发来的电报:“飞机18日到库木库都克送水(shuǐ),你们不要动,原地待命。”
接到电报(diànbào),大家都很兴奋。队员汪文先想把这一喜讯告诉(gàosù)彭加木,他拿着电文走出帐篷,却没有看到彭加木的身影。
他以为彭加木只是去附近解手了,于是又回帐篷(zhàngpéng)等待。一个小时后还未见彭加木回来,大家方(fāng)感觉有些不妙了。
此时,司机(sījī)王万轩(wángwànxuān)走出帐篷,到汽车上去取衣服。他突然发现右边的座位上有一张摊开的地图。这张地图是全队唯一一张地形图,彭加木一路上一直坐在这个(zhègè)位置,他是从不把这张地图随意丢放的。
王万轩把地图(dìtú)拿起收好,突见地图下面有一张纸条,上面写道:
“我往东去找水井(shuǐjǐng)。彭,17/6 10:30”
卫星(wèixīng)拍下的“地球之耳”罗布泊。
罗布泊的(de)神秘之处,并不仅仅在于它奇特(qítè)的地理构造,更源于它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湮灭在漫漫黄沙下的历史传说。
罗布泊历史上最繁华的一个时期,是在“楼兰(lóulán)王国”兴盛之时。楼兰古城地处罗布泊的西北侧,这里曾经(céngjīng)是丝绸之路南支的咽喉门户。
楼兰于公元前176年以前(yǐqián)建国、公元630年消亡,历时800多年。随着(suízhe)楼兰国的消亡,这里渐渐成为人迹罕至之地,丝绸之路的故道不复存在,罗布荒原逐渐被人们所遗忘(yíwàng)。
直到1900年3月,瑞典探险家斯文(sīwén)·赫定探险队沿着干枯的孔雀河左河床来到罗布荒原,意外(yìwài)地发现了隐藏在历史(lìshǐ)沙砾中一千多年的楼兰古城,这一“神迹”才重现于世。
斯文·赫定回到欧洲,向全世界公布了罗布荒原上的(de)“沙埋文明”,轰动一时。神秘的“楼兰(lóulán)”是(shì)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成就之一,而楼兰古国所在(suǒzài)的这一片罗布荒原,成为了世界探险家趋之若鹜的神秘地带。
斯文·赫定曾在他那部著名的《亚洲腹地探险8年》一书中写道:“罗布泊使我惊讶,它像座仙湖(xiānhú),水面像镜子一样,在和煦的阳光(yángguāng)下,我乘舟而行,如(rú)神仙一般。”
作为此地最大的(de)沙漠咸湖,罗布泊也因此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。
上世纪初叶,罗布泊的“游移之谜(zhīmí)”曾引起世界学术界的极大争论。
最早(zuìzǎo)到新疆(xīnjiāng)考察的中外科学家们曾对罗布泊(luóbùpō)的确切位置争论不休,斯文·赫定认为罗布泊存在南北湖区,由于(yóuyú)入湖河水带有大量泥沙,沉积后抬高了湖底,原来的湖水就自然向另一处更低的地方流去,又过许多年,抬高的湖底会由于风蚀再次降低,湖水再度回流,这个周期为1510年,所以(suǒyǐ),他认为罗布泊是一个在沙漠中不断游移的湖。
斯文·赫定这(zhè)一学说,在(zài)当时曾得到(dédào)了世界普遍认可。“游移之谜”给罗布泊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,这片幽灵般的湖泊,再一次引起了全世界探险家的极大兴趣。
1927年,中国科学家第一次靠近(kàojìn)了这片“幽灵湖泊”。斯文·赫定在筹备第六次中亚考察时,决定由中瑞两国共同(gòngtóng)组成一个(yígè)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。时任北京大学教务长的知名学者徐炳旭(xúbǐngxù)担任中方团长,团中尽数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专家,如地质与古生物学家丁道衡、考古学家黄文弼、地理学家(dìlǐxuéjiā)陈宗器等。
这次考察从1927年持续到1933年,考察队先后在罗布泊、吐鲁番和塔里木盆地(tǎlǐmùpéndì)进行考古调查(diàochá)和部分试掘,撰写了《罗布淖尔考古记(jì)》、《吐鲁番考古记》、《塔里木盆地考古记》等,在国内出版,引起很大反响(fǎnxiǎng)。
此后的(de)很长一段时间,罗布泊的研究湮灭于连年战火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9年,罗布荒原终于又(yòu)迎来了一支新的科学考察队。
从1956年到1959年,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(zōnghé)考察队对塔里木下游和罗布泊地区(dìqū)进行了新中国成立后最大规模的一次综合考察,当时,队员们是乘着舟进入(jìnrù)罗布泊的。
夏训诚因被分在北疆(běijiāng)组考察,遗憾地与当时(dāngshí)尚未干涸的(de)罗布泊失之交臂。他说,那次考察留下了人类在罗布泊荡舟的最后记录,“由于1952年在拉依河筑坝,使塔里木河和孔雀河(kǒngquèhé)彻底分流,孔雀河下泄的河水逐渐断绝,罗布泊在上世纪(shìjì)70年代初全部干涸了,终结了它作为一个湖泊的历史。”
那次考察后不久,罗布泊被定为核试验场,从此成为军事禁区。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,任何与核试验无关的人都不得进入(jìnrù)这个地区(dìqū)。
彭加木也没有参加(cānjiā)那次考察。那时他正在上海(shànghǎi)的医院中,与恶性肿瘤、癌细胞搏斗着。
“彭加木”这个名字,也刚刚出现(chūxiàn)不久。
1947年,22岁的广东番禺青年彭家睦从中央大学(1949年更名(gēngmíng)南京大学)农学院毕业,到(dào)北京大学农学院任教,专攻农业化学。1949年,他被分配(fēnpèi)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。
1956年初,中央发出了“向(xiàng)科学进军”的号召,正当(zhèngdāng)此时,彭家睦迎来了一个对他个人发展千载难逢的机会。
科学院的领导研究决定,派年轻的彭家睦到莫斯科(mòsīkē)去(qù)学习一项新的技术——核磁共振,办理完出国手续即刻便要动身。
能够去苏联学习,无疑是一个好机会,彭家睦自然是高兴极了,但是他(tā)马上又(yòu)陷入了两难的选择中。
就在这个当口,中国科学院为了开发祖国边疆的丰富资源,组织了综合考察委员会。这个委员会此时正在“招兵买马(zhāobīngmǎimǎ)”,吸收各方面(fāngmiàn)科技人才,准备(zhǔnbèi)组成若干小组,分赴祖国边疆各地进行实地考察。
究竟是去国外留学还是去边疆考察,31岁的彭家(péngjiā)睦面临重要的人生选择,经过反复(fǎnfù)考虑后,他选择了后者。
彭家睦曾经亲笔写下作出这一选择的(de)(de)原因:“我必须在出国和到边疆之间立刻做出选择,我考虑的结果,认为出国学习的任务虽然重要,但可以由别的同志来完成,别的同志也乐于去(qù)干(gàn),为了让科学在祖国遍地开花,作为一个共产党员,应当选择到最艰苦的地方去。”
在同样(tóngyàng)毕业于南京大学的(de)夏训诚看来,彭家睦当年的选择着实令人敬佩:“上海的科研条件自然(zìrán)比边疆要好得多,而且他当时在植物学领域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,但是为了边疆的科研,他甘愿(gānyuàn)做铺路石子。”
1956年3月, 彭家睦的申请正式得到了批准,他如愿以偿地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(shēngwùhuàxué)研究所调到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工作(gōngzuò),当时的职务是助理(zhùlǐ)研究员。
此时,他的户口也从上海迁到了北京(běijīng)。在(zài)迁户口时,彭家睦打(dǎ)了一个改名报告,把“彭家睦”改为了“彭加木”。从此,他一直用“彭加木”这个名字。
实际上,在迁户口之前,他就已经在使用“彭加木”的名字了。为了争取参加中(zhōng)国边疆科考,彭加木直接写信给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。他在信中(xìnzhōng)写道:“我具有从荒野中踏出一条(yītiáo)道路(dàolù)的勇气。”在信的末尾,署名并不是“彭家睦”,而是“彭加木”。
从“彭家睦”到“彭加木”,其实是他表示“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”的决心。彭加木认为“家睦”只是希望家庭和睦,着眼于(zhuóyǎnyú)小家(xiǎojiā),太狭隘(xiáài)了;他要跳出小家庭,为边疆“添草加木”。
那一年的秋天,彭加木第一次来到(láidào)乌鲁木齐。当时(dāngshí)新疆的科研事业只是有了一点点萌芽,而在生物化学研究方面几乎是一个空白。一到新疆,彭加木就帮助当地筹建了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。然而(ránér),这个豪情万丈的垦荒者,却突然遭受了一个重大打击(dǎjī)。
1957年初,彭加木突然被查出患有纵隔障恶性肿瘤,返回上海治疗。以当时的医疗条件,医生们根据(gēnjù)有限的医学文献和病例判断(pànduàn),彭加木最多只能(zhǐnéng)活两年。
祸不单行的是,在住院期间,彭加木又(yòu)被查出还患有另一种恶性肿瘤——网状细胞(xìbāo)淋巴瘤,患这种病一般只能活几个月。
等于是被判了死刑的彭加木却没有(méiyǒu)被病魔打倒(dǎdǎo),一年以后,他竟然奇迹般地康复了。虽然医生严令禁止他离开上海(shànghǎi),但是彭加木刚一出院就接二连三地要求“放虎归山”,回到新疆去工作。
1958年的春天,一个险些被癌症夺去生命的人,又踏上了西行(xīxíng)的旅程,彭加木与罗布泊也从此正式(zhèngshì)结缘。
彭加木在新疆工作期间,一共有过四次对(duì)新疆地区的大规模考察(kǎochá)。这些考察包括人文、地理、生物、矿产资源、文物古籍、风土民情等。
1959年,彭加木(péngjiāmù)曾到过罗布泊北部地区,采集过土壤标本。经过化验,他发现此地土壤中的(de)钾含量(hánliàng)非常高。1964年,他对流入罗布泊的孔雀河、塔里木河、车尔臣河等河流进行了综合考察。参与这次考察的共有四个人(rén),由彭加木带队(dàiduì),此外还有新疆化学所的两名科研工作者和一名司机。考察从9月上旬到10月下旬,历时40多天,行程近5000公里(gōnglǐ)。
在(zài)对流入罗布泊的(de)几条河的钾含量作了初步分析后,彭加木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——罗布泊极有可能蕴藏巨大储量的钾盐。
钾盐是农用钾肥的生产原料,在我国属大宗紧缺(jǐnquē)矿种,中国(zhōngguó)境内可溶性钾盐资源严重不足,需要大量进口。
彭加木同时判断,在罗布泊的(de)盐层中,还含有宝贵的原料,比如制造(zhìzào)飞机所需的镁,稀有金属锂(lǐ)等。另外,那里还可能有重水资源。重水是重要的中子减速器,无论是建造原子能反应堆还是制造原子弹都会用到它(tā),此外,它还是制造氢弹的原料,属于重要的战略资源。
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,我国(wǒguó)在钾盐勘查方面投入(tóurù)大量(dàliàng)的人力和经费,除了在柴达木盆地取得重大突破外,其它(qítā)地区成果甚微,以致出现了中国“无钾论”的看法。中国是否能再找到大型钾盐矿床,一直是科学界关注的焦点。
那次考察中,在塔里木河下游,彭加木发现河水(héshuǐ)的(de)钾含量在逐渐增加。他根据气象资料推算出河水的流量,并从河水的流量数据(shùjù)推算出河流搬运钾元素的大约值,由此(yóucǐ)估算出罗布泊每年会积聚约75万吨钾,可能还含有其他稀有金属和重水等资源。
夏训诚说,彭加木是(shì)第一个提出罗布泊有钾盐矿(kuàng)的(de)人。如果罗布泊果真富集钾盐矿,这里就不再是人迹罕至的荒漠,而是一个巨大的“聚宝盆”。
在新疆进行这一次考察时,彭加木39岁,在罗布泊寻找钾盐矿成为了他对这片神秘(shénmì)区域最初的研究目标。遗憾(yíhàn)的是,由于“文革”的影响,他对罗布泊的研究计划(jìhuà)也不得不搁浅了十余年。
“地球之耳”的(de)神秘大门对彭加木再次打开的时候,他已经54岁了(le)。对一个科学家来说,这个年龄还(hái)算年轻。然而,重新走进这道大门仅仅一年时间,彭加木的生命戛然而止。
1979年的(de)冬天,刚刚率领科学考察队从(cóng)天山最高峰——托木尔峰归来的夏训诚,突然接到新疆考古所副所长穆舜英打来的电话。
穆舜英在电话中说,由中日联合组成的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即将(jíjiāng)来新疆,在罗布泊(luóbùpō)附近进行(jìnxíng)实地拍摄。夏训诚被聘请为“顾问”,要组成一个“先遣队”进入罗布泊打个前站。
罗布泊在上世纪60年代(niándài)被列为军事禁区,又因“文革”的关系,此地的科学考察一直处于停滞状态。对夏(duìxià)训诚来说,能够再次进入罗布泊就像是“圆梦”一样,兴奋之余,他突然想到(xiǎngdào)了老朋友彭加木。
致力于沙漠治理的夏训诚从上(shàng)世纪50年代起就一直在新疆进行考察和研究,因工作关系与彭加木(péngjiāmù)结识多年,“我知道他一直想去罗布泊找钾盐,这个机会千载难逢(qiānzǎinánféng)。”夏训诚说。
于是,他(tā)把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告诉了(le)彭加木,彭加木当时竟高兴得跳了起来,连说“太好了(tàihǎole)”。夏训诚现在仍然记得,彭加木当时像孩子一样握着他的手,一直恳求他帮忙,与有关单位(dānwèi)联系参加这次考察。
夏训诚回忆,当时联系的过程颇为复杂,罗布泊毕竟是几十年的军事禁区。“据我了解,《丝绸之路(sīchóuzhīlù)》摄制组此行进入(jìnrù)罗布泊,是邓小平(dèngxiǎopíng)同志亲自(qīnzì)批准的。”最终,执着的彭加木还是得到了这次进入罗布泊的机会。
“先遣队”不是一个(yígè)严格(yángé)的科学考察的组织,但是每(měi)一个队员都有自己心里的“小算盘”,作为地理工作者,夏训诚关注罗布泊的自然环境变迁情况;而对于彭加木来说,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延续上世纪60年代未完成的考察计划,在罗布泊寻找钾盐(jiǎyán)。
这是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,罗布泊(luóbùpō)地(dì)区第一次向非军事人员开放。20余天的时间(shíjiān)里,6辆吉普车组成的车队穿过了沉寂的荒原,穿过楼兰古城和白龙堆雅丹,在完成了几次横向与纵向穿插罗布泊西部的考察后,“先遣队”成功地回到了乌鲁木齐的基地(jīdì)。
在离开基地的前一天(qiányītiān),彭加木向夏训诚提议,由他俩(tāliǎ)牵头,上书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建议正式组建考察队,对罗布泊进行(jìnxíng)全面的综合考察。
彭加木此时提出考察计划,已(yǐ)不仅仅(bùjǐnjǐn)为了他寻找已久的钾盐矿。一个多世纪以来(yǐlái),俄国人、瑞典人、日本人一次一次来到罗布泊(luóbùpō)考察、探险,写出了许多关于罗布泊的文章,以至于国外竟有一种言论:“罗布泊在中国,而罗布泊的研究在外国”。彭加木向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表示,要夺回中国科学家在罗布泊的发言权。
几天以后,彭加木正式调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,这无疑对(duì)组建罗布泊考察队起到了积极的(de)作用。
1980年初(niánchū),通过各方面的努力,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(fēnyuàn)正式下达了成立(chénglì)罗布泊科学考察队的文件,并决定由彭加木担任队长,夏训诚担任副队长。
彭加木心中多年的夙愿,即将(jíjiāng)达成。
根据计划(jìhuà),这次对罗布泊的综合考察分三次进行。1980年的第一次考察主要(zhǔyào)是路线考察,时间定在1980年的5、6月间,第二年再进行后两次(liǎngcì)考察。
“第一次考察之所以(zhīsuǒyǐ)定在(zài)这个月份,是因为这时正是沙漠荒原风沙季节和酷热季节的‘空档’。”夏训诚说。但是他认为当时的计划并(bìng)不周全,“我们当时不知道,实际上罗布泊地区(dìqū)并没有这种‘空档’,或者说很短促。”
在制定计划的同时,考察队正式开始“招兵买马”。夏训诚主持组建队伍的工作,他从新疆分院的好几个部门抽调了6名专业(zhuānyè)人员和3名司机、一名后勤(hòuqín),这十位同志组成(zǔchéng)了一支罗布泊科学考察队。
5月3日,由彭加木率队,罗布泊(luóbùpō)科学考察队从乌鲁木齐出发,正式向罗布泊进发了(le)。因为在出发前突然接到去美国考察的通知,夏训诚遗憾地(dì)错过了参加第一次路线考察的机会。
夏训诚直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,建议组建考察队时,彭加木曾悲愤地说(dìshuō):“我不希望在罗布泊全是外国人(wàiguórén)留下的足迹,作为一个中国人,我就觉得应该把自己的骨头(gútou)埋在罗布泊,使它的土壤多一点(duōyìdiǎn)中国的有机质!”
这不是一句玩笑,而是彭加木(péngjiāmù)的真实想法。如果说科学探索总(zǒng)需要牺牲,他是在进入罗布泊之前,就已经作好了牺牲准备的。
夏训诚万万没有想到,仅仅一个多月以后,彭加木的话(dehuà)一语成谶。
作为对罗布泊的(de)第一次深入性考察,彭加木的计划是十分大胆的。
他打算率队从北至南,纵穿(zòngchuān)罗布泊。在他看来,只有纵穿罗布泊,才能弄清这个神秘之地(zhīdì)的真实面目。
但是(dànshì),第一次纵穿并未成功。彭加木(péngjiāmù)在日记中写道:“我们在5月9日开始进入湖区,有(yǒu)一个七人(qīrén)探路小分队,自北往南纵贯罗布泊湖底。湖表面已没有水,有些地面松软陷车,有些地面则比较平整。汽车车胎由于锋利的盐晶块切割,损耗过大,无法继续前进。”
那天晚上,考察队只能原地宿营。因为当时(dāngshí)所带的汽油和水(shuǐ)都消耗了不少,彭加木只得决定原路返回,重新补充油、水之后再度前进。
湖底的(de)盐晶块是前进的极大阻碍,最终用来给考察队(kǎocháduì)开路的,竟然是队员们手中十几(shíjǐ)磅重的大铁锤。这个方法也是彭加木提出(tíchū)的,最初遭到队员们的一致反对,大家认为在罗布泊湖底用铁锤人工开路简直是天方夜谭。
事实证明(shìshízhèngmíng),彭加木的意见是正确的。5月30日,考察队重新出发,又一次到了这个地区,大家拿着铁锤下车,一锤一锤地把车轮前的盐晶块(yánjīngkuài)砸碎。汽车(qìchē)颠簸前行,直到他们找到了古河道的入湖口,路(lù)才一下子平顺了起来,盐晶块对车行的阻碍得以解除。
汽车沿着古河道走了两天,终于完成了纵贯罗布泊的计划。沿途(yántú),考察队进行了简单的地质勘探,彭加木凿开盐壳,从下面瓦蓝色(lánsè)的沙层中取出一个水样(shuǐyàng),兴奋地对大家说:“这里可能有‘重水’!”能够在地域广阔的罗布泊找到重水资源,这无疑(wúyí)是(shì)对中国核物理工业发展的一个巨大贡献。
彭加木曾这样评价此次纵穿罗布泊的(de)经历(jīnglì):“此次胜利的穿越盐壳地带,自北而南纵贯罗布泊干涸湖底(húdǐ)成功,是一个很大的收获,这是前所未有的,对罗布泊洼地中心区域已经有了一些了解,可算(kěsuàn)得是敲开了罗布泊的大门。”
考察队在6月5日到达(dàodá)了考察的最后一站——米兰农场。
进入米兰(mǐlán)农场(nóngchǎng)以后,考察队的队员们如同卸下了千斤重担。按原定的方案,在米兰农场休息几天后考察队就可以启程回乌鲁木齐了。
就在此时,彭加木突然向队员们提出了(le)“东进计划”。
这次考察原计划到7月3日结束,还有近一个月时间。彭加木建议(jiànyì)暂不回乌鲁木齐,利用剩下的这些时间一鼓作气(yīgǔzuòqì)完成对(duì)整个罗布泊地区的考察。
1979年冬天,彭加木作为纪录片《丝绸之路》的“先遣队”成员之一,曾完成了对罗布泊西部的考察(kǎochá),这次,考察队又从罗布泊的中部纵穿(zòngchuān)而过,他计划在余下一个月(yígèyuè)的时间里,沿罗布泊东部北上,穿过疏流河(liúhé)直至敦煌,完成对罗布泊地区的全面考察,最后再(zài)回乌鲁木齐。
虽然队员们已经非常疲惫,但最终大家还是(háishì)决定采纳彭加木的建议。
彭加木通过电报向中科院新疆分院(fēnyuàn)汇报请求批准。新疆分院接到电报后,经研究同意他们的计划,但(dàn)一再嘱咐(yīzàizhǔfù),一定要注意安全,有情况及时与基地联系。
在准备出发,装(zhuāng)汽油和水的时候,彭加木提议可以多装一桶汽油,少装一桶水。原因是从地图上看,到了库木库都克这个地方(dìfāng)有水井(shuǐjǐng),可以在这个地方补充水源。根据路程(lùchéng)计算,到库木库都克只有400多公里,最多两天即可赶到。
然而,在这一段路上,考察队(kǎocháduì)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麻烦。
6月11日,考察队一早从米兰出发,一直赶路到天黑。十几个小时,车子只走了(le)58公里(lǐ),还不到计划行程的(de)一半。一路都是松软的沙石地,三辆车不是这辆陷进了泥坑,就是那辆困(kùn)在了沙窝子,有时候几个小时才能把一辆车从泥坑里弄出来,此后的几天里也都是如此,结果,本来预计两天的路程考察队走了整整(zhěngzhěng)6天。
6月16日下午6时左右,考察队终于赶到(gǎndào)了库木库都克,此时大家都已是筋疲力尽,却不得不再次外出——由于行程(xíngchéng)被耽搁,出发时带的汽油和水此时都快要消耗(xiāohào)殆尽了。
“库木库都克”是维吾尔语(wéiwúěryǔ)“沙井”的意思。从考察队带的那张地图看,这里确实标有水井。考察队支好帐篷,休息了一会儿(yīhuìer),便立刻出发去找水(zhǎoshuǐ)。
让彭加木和队员们大为失望的是,从下午找到晚上,这片茫茫的沙漠中根本没有水(shuǐ)井的踪影。眼下,所剩的汽油只能供三辆(sānliàng)车行驶几十公里;水,则只剩下一汽油桶,且(qiě)已变质,难以饮用。
没有水和汽油,考察队员们即刻就面临生命危险,几乎陷入绝境的(de)考察队决定向部队紧急求助(qiúzhù)。
6月16日晚上10时10分,彭加木亲自起草了发给部队的告急电报:“我们已到(dào)达了库木库都克以西大约十公里。我们缺油和水(shuǐ),请求紧急(jǐnjí)支援油、水各500公斤,现有的水只能维持到18日。”
电报发出后(hòu),正在大家焦急等待回复的时候(shíhòu),彭加木提出了新的建议。
一向节俭的彭加木认为,用直升机运水(yùnshuǐ)太贵了(le)。直升机飞行一小时,在那个年代要花2000多块钱,从驻军基地到宿营地,来回(láihuí)要飞好几个小时。他建议大家自力更生,尽量自己找水。
不久前,他和别人闲聊中听说,年初的时候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曾经在“八一泉(quán)”加过(jiāguò)水。“八一泉”位于疏流河故道北岸,在库木库都克东北约30公里处(chù)。
所以,彭加木建议开车(kāichē)再(zài)往东面去找一次水井,但是这个建议遭到了(le)队员们的全体反对。大家计算了一下,这一路线要用掉(diào)大概半桶汽油,大家一致认为不能再消耗本已不多的汽油,应该等与部队联系上以后,再作打算。
第二天上午(shàngwǔ)11点半,考察队收到了部队发来的电报:“飞机18日到库木库都克送水(shuǐ),你们不要动,原地待命。”
接到电报(diànbào),大家都很兴奋。队员汪文先想把这一喜讯告诉(gàosù)彭加木,他拿着电文走出帐篷,却没有看到彭加木的身影。
他以为彭加木只是去附近解手了,于是又回帐篷(zhàngpéng)等待。一个小时后还未见彭加木回来,大家方(fāng)感觉有些不妙了。
此时,司机(sījī)王万轩(wángwànxuān)走出帐篷,到汽车上去取衣服。他突然发现右边的座位上有一张摊开的地图。这张地图是全队唯一一张地形图,彭加木一路上一直坐在这个(zhègè)位置,他是从不把这张地图随意丢放的。
王万轩把地图(dìtú)拿起收好,突见地图下面有一张纸条,上面写道:
“我往东去找水井(shuǐjǐng)。彭,17/6 10:30”
 彭加木失踪前留下的最后一张(yīzhāng)字条。
纸条显然是这天上午写下的,日(rì)期上的“17”日还是“16”日改写的,大概是彭加木曾经一时写错了日期。此时大家(dàjiā)才发现,彭加木的黄帆布包和(hé)那只能装两公斤水的水壶也不见了。
队员(duìyuán)们怎么也想不到,这张字条,竟是彭加木(péngjiāmù)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。
那天下午,所有队员出动寻找彭加木,他们按照(ànzhào)字条的指引向东寻,沿着彭加木那双42号翻毛皮靴在沙地中留下的脚印走了将近8公里,都不见他的踪影。脚印却(què)最终消失在盐(yán)壳地的边缘,搜寻(sōuxún)一下子失去了方向。
为了(le)跟部队及时电报联系,队员们只得在晚上10点回到了营地,大家在营地里燃起篝火,把吉普车开到最高处,向东方开亮(kāiliàng)了车前大灯,并每隔一小时(xiǎoshí)向空中发射一次信号弹。
队员们希望,彭加木可以循着亮光,找到(zhǎodào)营地的方向。
然而,彭加木消瘦的身影再也(zàiyě)没有出现在队员们的视线中。
6月18日凌晨两点,考察队(kǎocháduì)正式(zhèngshì)发出电报:彭加木走失,下落不明。
此时,距离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已经过去了16个小时。
18日中午,直升机载着500公斤水找到了考察队的露营地,队员们(men)获救了。第二天,部队又(yòu)给他们送来三桶汽油。但是,经过队员们持续十几个小时的寻找,没有任何(rènhé)结果。
搜寻中唯一的突破,是在一片岩石间(jiān)发现了一张椰子奶油糖的糖纸,旁边(pángbiān)还有人坐过的痕迹。队友们知道,这个牌子的奶油糖是彭加木随身携带的,但是沿着旁边的脚印(jiǎoyìn)追踪了几十公里后(hòu),脚印又在盐壳边缘消失了。
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于6月18日下午6点得到了彭加木失踪的消息。晚上12点,副院长(yuànzhǎng)陈善明带着两名干部,由两个司机轮流开车连夜往马兰基地(jīdì)(jīdì)赶。19日早晨7点一到基地,他就会同基地的几位领导(lǐngdǎo)组成了救援领导小组,组织对彭加木的救援工作。
一个大规模的寻找彭加木的战役拉开了(le)帷幕。
根据夏训诚的回忆,当年较大规模的寻找,一共有四次(sìcì)。
第一次寻找(xúnzhǎo)是在彭加木刚失踪时,6月18日到19日,队员们在宿营地周围(zhōuwéi)进行了搜寻。
第二次寻找是在6月(yuè)20日到26日,在收到(shōudào)呼救讯号后,当地部队和科考(kēkǎo)队员出动136人次,空军出动9架直升机、三架“安-2”型飞机,在出事地点东西50公里范围内进行地毯式低空搜寻。
第三次寻找是(shì)在7月(yuè)7日到8月2日,117人,48辆车,29架次飞机,搜索面积达到4000多平方公里。
“我参加的就是第三次(dìsāncì)搜寻,当时公安人员(gōngānrényuán)还特意带着六条警犬(jǐngquǎn)赶到了罗布泊。”夏训诚说,可惜因为当地天气太热,警犬也丧失了嗅觉,并没有找到彭加木的踪迹。
就在人们对彭加木的生还(shēnghuán)已经(yǐjīng)基本丧失了希望的时候,一家香港媒体竟然曝出新闻:失踪的彭加木在美国出现了。
彭加木失踪前留下的最后一张(yīzhāng)字条。
纸条显然是这天上午写下的,日(rì)期上的“17”日还是“16”日改写的,大概是彭加木曾经一时写错了日期。此时大家(dàjiā)才发现,彭加木的黄帆布包和(hé)那只能装两公斤水的水壶也不见了。
队员(duìyuán)们怎么也想不到,这张字条,竟是彭加木(péngjiāmù)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。
那天下午,所有队员出动寻找彭加木,他们按照(ànzhào)字条的指引向东寻,沿着彭加木那双42号翻毛皮靴在沙地中留下的脚印走了将近8公里,都不见他的踪影。脚印却(què)最终消失在盐(yán)壳地的边缘,搜寻(sōuxún)一下子失去了方向。
为了(le)跟部队及时电报联系,队员们只得在晚上10点回到了营地,大家在营地里燃起篝火,把吉普车开到最高处,向东方开亮(kāiliàng)了车前大灯,并每隔一小时(xiǎoshí)向空中发射一次信号弹。
队员们希望,彭加木可以循着亮光,找到(zhǎodào)营地的方向。
然而,彭加木消瘦的身影再也(zàiyě)没有出现在队员们的视线中。
6月18日凌晨两点,考察队(kǎocháduì)正式(zhèngshì)发出电报:彭加木走失,下落不明。
此时,距离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已经过去了16个小时。
18日中午,直升机载着500公斤水找到了考察队的露营地,队员们(men)获救了。第二天,部队又(yòu)给他们送来三桶汽油。但是,经过队员们持续十几个小时的寻找,没有任何(rènhé)结果。
搜寻中唯一的突破,是在一片岩石间(jiān)发现了一张椰子奶油糖的糖纸,旁边(pángbiān)还有人坐过的痕迹。队友们知道,这个牌子的奶油糖是彭加木随身携带的,但是沿着旁边的脚印(jiǎoyìn)追踪了几十公里后(hòu),脚印又在盐壳边缘消失了。
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于6月18日下午6点得到了彭加木失踪的消息。晚上12点,副院长(yuànzhǎng)陈善明带着两名干部,由两个司机轮流开车连夜往马兰基地(jīdì)(jīdì)赶。19日早晨7点一到基地,他就会同基地的几位领导(lǐngdǎo)组成了救援领导小组,组织对彭加木的救援工作。
一个大规模的寻找彭加木的战役拉开了(le)帷幕。
根据夏训诚的回忆,当年较大规模的寻找,一共有四次(sìcì)。
第一次寻找(xúnzhǎo)是在彭加木刚失踪时,6月18日到19日,队员们在宿营地周围(zhōuwéi)进行了搜寻。
第二次寻找是在6月(yuè)20日到26日,在收到(shōudào)呼救讯号后,当地部队和科考(kēkǎo)队员出动136人次,空军出动9架直升机、三架“安-2”型飞机,在出事地点东西50公里范围内进行地毯式低空搜寻。
第三次寻找是(shì)在7月(yuè)7日到8月2日,117人,48辆车,29架次飞机,搜索面积达到4000多平方公里。
“我参加的就是第三次(dìsāncì)搜寻,当时公安人员(gōngānrényuán)还特意带着六条警犬(jǐngquǎn)赶到了罗布泊。”夏训诚说,可惜因为当地天气太热,警犬也丧失了嗅觉,并没有找到彭加木的踪迹。
就在人们对彭加木的生还(shēnghuán)已经(yǐjīng)基本丧失了希望的时候,一家香港媒体竟然曝出新闻:失踪的彭加木在美国出现了。
 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地纪念碑前的纪念。
1980年10月11日(rì),香港《中报》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载了一则奇闻(qíwén)。
文中称,当年9月14日下午7时许,一个名叫周光磊(zhōuguānglěi)的“中国(zhōngguó)留美学者”和几名朋友在(zài)华盛顿的一家饭馆吃饭的时候,竟然看见了在罗布泊失踪半年之久的著名科学家——彭加木。
这篇写得有鼻子有眼的(de)“奇闻”立刻引起海内外一片哗然。为了澄清事实,新华社记者专门(zhuānmén)就此事进行了调查,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明确(míngquè)表示,她和彭加木从来就不认识周光磊这个人。
新华社记者的调查(diàochá)虽然揭穿了所谓“周光磊”编造的谎言,但关于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的原因,一时间出现了很多以讹传讹的坊间版本。
当时流传最广的,是说彭加木从罗布泊秘密逃亡美国(měiguó)或者苏联。
在夏训诚看来,这样的(de)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,“营地附近都(dōu)有军事雷达,怎么可能美国或者(huòzhě)苏联的飞机把他接走,我们的部队能不发现?”
在《追寻彭加木》一书中,叶永烈回忆,当年年底由国家组织的第四次对彭加木的搜寻(sōuxún),在某种意义上也有澄清流言的目的,如果能够找到彭加木的遗体,就能够击破别有用心(biéyǒuyòngxīn)的人对他(tā)失踪(shīzōng)原因的各种荒诞猜测。
但是,第四次搜寻(sōuxún)仍然无功而返。
在第四次大规模搜寻结束后,国务院批准了中国科学院对彭加木善后处理的(de)安排:在彭加木失踪的库木库都克建立一个(yígè)永久性的标志;授予他革命(gémìng)烈士称号;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隆重举行彭加木追悼会。
55岁的(de)彭加木就这样永远消失在罗布荒原,成为了墓碑上的一个(yígè)名字。
此后数年,坊间(fāngjiān)一再流出关于他失踪的(de)各种传闻,甚至曾有人(rén)怀疑彭加木是因找水跟队友起了争执,被人杀害。作为考察队的副队长,夏训诚虽然没有亲见失踪事件的发生,但他觉得这种猜测实在太过恶毒(èdú)。
他认为,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的原因,最大的可能性有两种。
其一,彭加木只身外出后(hòu)迷路,被流沙掩埋。根据当时的天气(tiānqì)记录,6月16日晚到17日上午,当地刮了一场8-10级(jí)的大风,黄沙滚动,天昏地暗。
其二,彭加木在雅丹(yǎdān)土包(tǔbāo)阴面休息时,被坍塌的(de)松土掩埋。在库木库都克附近地区,分布着数百个大小不等、高低不一的雅丹土包,这些雅丹土包由比较坚硬的黏土层和疏松的细沙层构成,一刮大风,沙层极易坍塌,把(bǎ)人埋到底下。
但这也仅仅是推测而已(éryǐ)。从彭加木失踪一直到今天,人们其实(qíshí)从未停止对他(tā)的寻找,不断有人在罗布沙漠中找到疑似彭加木的“干尸”,但是至今,没有任何一具能够确定是彭加木本人。
几十年间,人们一遍一遍用红色(hóngsè)的油漆,重新填涂他纪念碑上被风沙腐蚀掉色的碑文。人们永远不会忘记,彭加木曾用(céngyòng)生命开启(kāiqǐ)了中国科学界对神秘罗布泊的探寻。
彭加木带领考察队进行的那次成功的考察,为后来的第二、第三次综合考察打下了(le)(le)重要基础,中国科学家终于逐渐夺回(duóhuí)了罗布泊研究的发言权,改变了“罗布泊研究在国外”的被动局面。此外,根据(gēnjù)他当年提出(tíchū)的关于钾盐的观点,数十年后,中国科学家经过大量努力,果然在罗布泊发现了超大型钾盐矿床,查明的钾盐储量超过(chāoguò)了2.5亿吨,彻底摘掉了中国“无钾”的帽子。
直至(zhízhì)今日,彭加木仍旧身埋在(zài)茫茫沙海里。罗布荒原可以掩埋一个人的身体,却无法掩埋他带给人们的感动和(hé)激励:那种一往无前、不惧牺牲的科学精神,永远是指引人类文明进步的力量。
本文首发于(yú)《北京日报》2017年3月7日
原标题:沙海迷途——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之谜
来源:北京日报纪事微信(wēixìn)公众号
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地纪念碑前的纪念。
1980年10月11日(rì),香港《中报》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载了一则奇闻(qíwén)。
文中称,当年9月14日下午7时许,一个名叫周光磊(zhōuguānglěi)的“中国(zhōngguó)留美学者”和几名朋友在(zài)华盛顿的一家饭馆吃饭的时候,竟然看见了在罗布泊失踪半年之久的著名科学家——彭加木。
这篇写得有鼻子有眼的(de)“奇闻”立刻引起海内外一片哗然。为了澄清事实,新华社记者专门(zhuānmén)就此事进行了调查,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明确(míngquè)表示,她和彭加木从来就不认识周光磊这个人。
新华社记者的调查(diàochá)虽然揭穿了所谓“周光磊”编造的谎言,但关于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的原因,一时间出现了很多以讹传讹的坊间版本。
当时流传最广的,是说彭加木从罗布泊秘密逃亡美国(měiguó)或者苏联。
在夏训诚看来,这样的(de)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,“营地附近都(dōu)有军事雷达,怎么可能美国或者(huòzhě)苏联的飞机把他接走,我们的部队能不发现?”
在《追寻彭加木》一书中,叶永烈回忆,当年年底由国家组织的第四次对彭加木的搜寻(sōuxún),在某种意义上也有澄清流言的目的,如果能够找到彭加木的遗体,就能够击破别有用心(biéyǒuyòngxīn)的人对他(tā)失踪(shīzōng)原因的各种荒诞猜测。
但是,第四次搜寻(sōuxún)仍然无功而返。
在第四次大规模搜寻结束后,国务院批准了中国科学院对彭加木善后处理的(de)安排:在彭加木失踪的库木库都克建立一个(yígè)永久性的标志;授予他革命(gémìng)烈士称号;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隆重举行彭加木追悼会。
55岁的(de)彭加木就这样永远消失在罗布荒原,成为了墓碑上的一个(yígè)名字。
此后数年,坊间(fāngjiān)一再流出关于他失踪的(de)各种传闻,甚至曾有人(rén)怀疑彭加木是因找水跟队友起了争执,被人杀害。作为考察队的副队长,夏训诚虽然没有亲见失踪事件的发生,但他觉得这种猜测实在太过恶毒(èdú)。
他认为,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的原因,最大的可能性有两种。
其一,彭加木只身外出后(hòu)迷路,被流沙掩埋。根据当时的天气(tiānqì)记录,6月16日晚到17日上午,当地刮了一场8-10级(jí)的大风,黄沙滚动,天昏地暗。
其二,彭加木在雅丹(yǎdān)土包(tǔbāo)阴面休息时,被坍塌的(de)松土掩埋。在库木库都克附近地区,分布着数百个大小不等、高低不一的雅丹土包,这些雅丹土包由比较坚硬的黏土层和疏松的细沙层构成,一刮大风,沙层极易坍塌,把(bǎ)人埋到底下。
但这也仅仅是推测而已(éryǐ)。从彭加木失踪一直到今天,人们其实(qíshí)从未停止对他(tā)的寻找,不断有人在罗布沙漠中找到疑似彭加木的“干尸”,但是至今,没有任何一具能够确定是彭加木本人。
几十年间,人们一遍一遍用红色(hóngsè)的油漆,重新填涂他纪念碑上被风沙腐蚀掉色的碑文。人们永远不会忘记,彭加木曾用(céngyòng)生命开启(kāiqǐ)了中国科学界对神秘罗布泊的探寻。
彭加木带领考察队进行的那次成功的考察,为后来的第二、第三次综合考察打下了(le)(le)重要基础,中国科学家终于逐渐夺回(duóhuí)了罗布泊研究的发言权,改变了“罗布泊研究在国外”的被动局面。此外,根据(gēnjù)他当年提出(tíchū)的关于钾盐的观点,数十年后,中国科学家经过大量努力,果然在罗布泊发现了超大型钾盐矿床,查明的钾盐储量超过(chāoguò)了2.5亿吨,彻底摘掉了中国“无钾”的帽子。
直至(zhízhì)今日,彭加木仍旧身埋在(zài)茫茫沙海里。罗布荒原可以掩埋一个人的身体,却无法掩埋他带给人们的感动和(hé)激励:那种一往无前、不惧牺牲的科学精神,永远是指引人类文明进步的力量。
本文首发于(yú)《北京日报》2017年3月7日
原标题:沙海迷途——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之谜
来源:北京日报纪事微信(wēixìn)公众号
 彭加木(左)在新疆(xīnjiāng)考察时留影。
1980年6月(yuè)24日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里传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:著名科学家彭加木(péngjiāmù)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。
此时,距离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已经是第7天了。
也是在那一天,原中(zhōng)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(shāmò)研究所所长、时任罗布泊科学考察队副队长的夏训诚,在从北京返回乌鲁木齐的火车车厢中,听到了这个令他无法相信(xiāngxìn)的广播。
2017年记者采访夏训诚时,他已经83岁了。在北京的家中,当他回忆起当时(dāngshí)的情景,仍唏嘘(xīxū)不已。
“当时全车厢的人都(dōu)一下子安静了,我更是不敢相信,彭加木(péngjiāmù)是我的战友和同事,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,赶快赶回去,到现场(xiànchǎng)去找他,救他。”夏训诚说。
事实上,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当时本该和彭加木在一起(yìqǐ)。他们一起筹备了赴罗布泊的(de)科学考察(kǎochá)队,并制定了三期考察计划,夏训诚任副队长,彭加木任队长。但是就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,夏训诚突然接到了中国科学院的通知,让他参加考察团,赴美国进行沙漠考察。
在征求彭加木意见(yìjiàn)时,彭加木态度鲜明地劝说夏训诚赴美考察,不能失去难得的好机会(jīhuì)。“他还说,从长远看,这次(zhècì)进入罗布泊(luóbùpō)的项目考察,关键性的专业考察是在来年的第二次和第三次。”夏训诚回忆道,彭加木随信寄给他一百多张此前中国考察队在罗布泊拍摄的幻灯片(huàndēngpiàn),他建议夏训诚把这些照片带到美国去,并告诉全世界: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已经踏上(tàshàng)了罗布泊这块世界瞩目的神秘之地。
这些照片确实在(zài)当年的美国科学界引起了巨大轰动,然而让夏训诚万万没有(méiyǒu)想到的是,仅仅一个多月后,彭加木永远消失在罗布泊,再也不能兑现和他的科考(kēkǎo)之约了。
1980年的中国(zhōngguó),新闻传播还只限于报纸和广播,电视都尚未普及,发出第一篇关于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新闻报道的人,是(shì)新华社驻新疆分社记者赵全章。
1980年6月20日,赵全章到乌鲁木齐机场送人(sòngrén),新疆(xīnjiāng)八一农学院的副教授徐鹏告诉他(tā),自己无意间从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得知,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了。
这样的信息在(zài)当时是(shì)要严格保密的。出于记者的新闻敏感,赵全章在归途中,特地在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门口下了车(chē)。他在新疆分院值班室核实(héshí)了彭加木失踪的情况,写出了关于此事的第一篇新闻稿,但只是作为新华社内参报到了北京,并未准备公开发表。
由于是供领导看的内参,这篇新闻稿中提出搜索彭加木工作中的困难:只有一两架(liǎngjià)飞机,地面搜索人员也(yě)很(hěn)不够,意在呼吁加大搜索力量。
翌日——6月21日,新华社社长穆青看了内参上(shàng)这一新闻,当即决定:发公开稿(gǎo)。
经过中央领导批示后,新华社新疆分社(fēnshè)在6月23日晚上(wǎnshàng),发出了关于彭加木失踪的(de)第一条电讯。在此之前,中科院上海分院已经提前去看望了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,让她心里有所准备。
第二天,全国(quánguó)的媒体(méitǐ)都铺天盖地地以各种形式播发了这条新闻: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(yuànzhǎng)、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进入罗布泊地区进行科学考察的时候,不幸失踪。
消息一出,举(jǔ)国震惊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数次寻找的毫无结果,彭加木失踪成了当时全国最(zuì)牵动人心的事情。在彭加木失踪之处,附近的居民自发组织起寻人的队伍;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信雪片(xuěpiàn)般地飞向新疆,一时间,彭加木成为(chéngwéi)了家喻户晓(jiāyùhùxiǎo)的人物,许多人为他的事迹所感动和激励。
然而,彭加木并不是第一个在罗布泊倒下(dǎoxià)的人,也不是最后一个。
在过去的100多年间,罗布泊一直被视为一片神秘的土地。从19世纪末(shìjìmò)开始,这里就曾吸引一批又一批中外探险家千山万水地来到此地,探究这片沙漠深处的秘密。死亡的威胁,也不曾(bùcéng)挡住人们走近它(tā)的脚步。在彭加木失踪16年后,即将完成徒步穿越新疆罗布泊全境壮举的探险家余纯顺,在一场突然而(ér)至的沙暴中不幸遇难(bùxìngyùnàn)。
这片极具危险(wēixiǎn)的“死亡之海”,为何具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?
1964年(nián)10月16日,中国成功试验了一颗原子弹,随着惊天动地的(de)巨响,一朵巨大的蘑菇云从中国第一个(dìyígè)核试验基地——马兰基地升腾而起。
马兰基地所在(suǒzài)的位置(wèizhì),正是人迹罕至的罗布泊沙漠。罗布泊最广为人知的原因,就是因为这片荒漠曾被作为核试验场。
其实,漫长的历史中,罗布泊并非一直如此干旱和荒凉。从它(tā)名字中的“泊”就能看出,这里曾经是(shì)个水源丰沛之地。
在中国的(de)史料典籍中,罗布泊曾有(yǒu)过许多名称:有的因它(tā)的特点而命名,如泑泽、盐泽、涸海等;有的因它的位置而得名,如蒲昌海、牢兰海、孔雀海、洛普池等。元代以后,此地被称为罗布淖尔。
罗布淖尔系蒙古语音译名,意为(yìwèi)多水汇集之湖。罗布泊(luóbùpō)位于塔里木盆地的最低处,海拔780公尺,塔里木河、孔雀河、车尔臣河、疏勒河等汇集于此(cǐ),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咸水湖。
在历史上,罗布泊(luóbùpō)的最大(dà)面积为5350平方公里,曾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湖,面积仅次于青海湖。
水量丰沛的罗布泊“广袤三百里,其水亭居,冬夏不增减”,可见(kějiàn)它当时的丰盈,古人甚至(shènzhì)曾误认为罗布泊为黄河的上源,这种(zhèzhǒng)说法从先秦至清末,流传了2000多年。
直到20世纪(shìjì)中后期,塔里木河流量减少,罗布泊周围沙漠化严重。20世纪70年代(niándài)末,罗布泊完全干涸。
1972年7月,从美国宇航局发射的地球资源卫星拍摄(pāishè)的照片上,人类第一次看到了罗布泊的全貌(quánmào)。
照片(zhàopiān)中干涸的罗布泊竟酷似人的一只耳朵,不但有耳轮(ěrlún)、耳孔,甚至还有耳垂。罗布泊因此被誉为“地球之耳”。事实上,这种奇特的地貌是湖水(húshuǐ)迅速退缩而形成的。
彭加木(左)在新疆(xīnjiāng)考察时留影。
1980年6月(yuè)24日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里传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:著名科学家彭加木(péngjiāmù)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。
此时,距离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已经是第7天了。
也是在那一天,原中(zhōng)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(shāmò)研究所所长、时任罗布泊科学考察队副队长的夏训诚,在从北京返回乌鲁木齐的火车车厢中,听到了这个令他无法相信(xiāngxìn)的广播。
2017年记者采访夏训诚时,他已经83岁了。在北京的家中,当他回忆起当时(dāngshí)的情景,仍唏嘘(xīxū)不已。
“当时全车厢的人都(dōu)一下子安静了,我更是不敢相信,彭加木(péngjiāmù)是我的战友和同事,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,赶快赶回去,到现场(xiànchǎng)去找他,救他。”夏训诚说。
事实上,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当时本该和彭加木在一起(yìqǐ)。他们一起筹备了赴罗布泊的(de)科学考察(kǎochá)队,并制定了三期考察计划,夏训诚任副队长,彭加木任队长。但是就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,夏训诚突然接到了中国科学院的通知,让他参加考察团,赴美国进行沙漠考察。
在征求彭加木意见(yìjiàn)时,彭加木态度鲜明地劝说夏训诚赴美考察,不能失去难得的好机会(jīhuì)。“他还说,从长远看,这次(zhècì)进入罗布泊(luóbùpō)的项目考察,关键性的专业考察是在来年的第二次和第三次。”夏训诚回忆道,彭加木随信寄给他一百多张此前中国考察队在罗布泊拍摄的幻灯片(huàndēngpiàn),他建议夏训诚把这些照片带到美国去,并告诉全世界: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已经踏上(tàshàng)了罗布泊这块世界瞩目的神秘之地。
这些照片确实在(zài)当年的美国科学界引起了巨大轰动,然而让夏训诚万万没有(méiyǒu)想到的是,仅仅一个多月后,彭加木永远消失在罗布泊,再也不能兑现和他的科考(kēkǎo)之约了。
1980年的中国(zhōngguó),新闻传播还只限于报纸和广播,电视都尚未普及,发出第一篇关于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新闻报道的人,是(shì)新华社驻新疆分社记者赵全章。
1980年6月20日,赵全章到乌鲁木齐机场送人(sòngrén),新疆(xīnjiāng)八一农学院的副教授徐鹏告诉他(tā),自己无意间从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得知,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了。
这样的信息在(zài)当时是(shì)要严格保密的。出于记者的新闻敏感,赵全章在归途中,特地在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门口下了车(chē)。他在新疆分院值班室核实(héshí)了彭加木失踪的情况,写出了关于此事的第一篇新闻稿,但只是作为新华社内参报到了北京,并未准备公开发表。
由于是供领导看的内参,这篇新闻稿中提出搜索彭加木工作中的困难:只有一两架(liǎngjià)飞机,地面搜索人员也(yě)很(hěn)不够,意在呼吁加大搜索力量。
翌日——6月21日,新华社社长穆青看了内参上(shàng)这一新闻,当即决定:发公开稿(gǎo)。
经过中央领导批示后,新华社新疆分社(fēnshè)在6月23日晚上(wǎnshàng),发出了关于彭加木失踪的(de)第一条电讯。在此之前,中科院上海分院已经提前去看望了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,让她心里有所准备。
第二天,全国(quánguó)的媒体(méitǐ)都铺天盖地地以各种形式播发了这条新闻: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(yuànzhǎng)、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进入罗布泊地区进行科学考察的时候,不幸失踪。
消息一出,举(jǔ)国震惊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数次寻找的毫无结果,彭加木失踪成了当时全国最(zuì)牵动人心的事情。在彭加木失踪之处,附近的居民自发组织起寻人的队伍;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信雪片(xuěpiàn)般地飞向新疆,一时间,彭加木成为(chéngwéi)了家喻户晓(jiāyùhùxiǎo)的人物,许多人为他的事迹所感动和激励。
然而,彭加木并不是第一个在罗布泊倒下(dǎoxià)的人,也不是最后一个。
在过去的100多年间,罗布泊一直被视为一片神秘的土地。从19世纪末(shìjìmò)开始,这里就曾吸引一批又一批中外探险家千山万水地来到此地,探究这片沙漠深处的秘密。死亡的威胁,也不曾(bùcéng)挡住人们走近它(tā)的脚步。在彭加木失踪16年后,即将完成徒步穿越新疆罗布泊全境壮举的探险家余纯顺,在一场突然而(ér)至的沙暴中不幸遇难(bùxìngyùnàn)。
这片极具危险(wēixiǎn)的“死亡之海”,为何具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?
1964年(nián)10月16日,中国成功试验了一颗原子弹,随着惊天动地的(de)巨响,一朵巨大的蘑菇云从中国第一个(dìyígè)核试验基地——马兰基地升腾而起。
马兰基地所在(suǒzài)的位置(wèizhì),正是人迹罕至的罗布泊沙漠。罗布泊最广为人知的原因,就是因为这片荒漠曾被作为核试验场。
其实,漫长的历史中,罗布泊并非一直如此干旱和荒凉。从它(tā)名字中的“泊”就能看出,这里曾经是(shì)个水源丰沛之地。
在中国的(de)史料典籍中,罗布泊曾有(yǒu)过许多名称:有的因它(tā)的特点而命名,如泑泽、盐泽、涸海等;有的因它的位置而得名,如蒲昌海、牢兰海、孔雀海、洛普池等。元代以后,此地被称为罗布淖尔。
罗布淖尔系蒙古语音译名,意为(yìwèi)多水汇集之湖。罗布泊(luóbùpō)位于塔里木盆地的最低处,海拔780公尺,塔里木河、孔雀河、车尔臣河、疏勒河等汇集于此(cǐ),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咸水湖。
在历史上,罗布泊(luóbùpō)的最大(dà)面积为5350平方公里,曾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湖,面积仅次于青海湖。
水量丰沛的罗布泊“广袤三百里,其水亭居,冬夏不增减”,可见(kějiàn)它当时的丰盈,古人甚至(shènzhì)曾误认为罗布泊为黄河的上源,这种(zhèzhǒng)说法从先秦至清末,流传了2000多年。
直到20世纪(shìjì)中后期,塔里木河流量减少,罗布泊周围沙漠化严重。20世纪70年代(niándài)末,罗布泊完全干涸。
1972年7月,从美国宇航局发射的地球资源卫星拍摄(pāishè)的照片上,人类第一次看到了罗布泊的全貌(quánmào)。
照片(zhàopiān)中干涸的罗布泊竟酷似人的一只耳朵,不但有耳轮(ěrlún)、耳孔,甚至还有耳垂。罗布泊因此被誉为“地球之耳”。事实上,这种奇特的地貌是湖水(húshuǐ)迅速退缩而形成的。
 卫星(wèixīng)拍下的“地球之耳”罗布泊。
罗布泊的(de)神秘之处,并不仅仅在于它奇特(qítè)的地理构造,更源于它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湮灭在漫漫黄沙下的历史传说。
罗布泊历史上最繁华的一个时期,是在“楼兰(lóulán)王国”兴盛之时。楼兰古城地处罗布泊的西北侧,这里曾经(céngjīng)是丝绸之路南支的咽喉门户。
楼兰于公元前176年以前(yǐqián)建国、公元630年消亡,历时800多年。随着(suízhe)楼兰国的消亡,这里渐渐成为人迹罕至之地,丝绸之路的故道不复存在,罗布荒原逐渐被人们所遗忘(yíwàng)。
直到1900年3月,瑞典探险家斯文(sīwén)·赫定探险队沿着干枯的孔雀河左河床来到罗布荒原,意外(yìwài)地发现了隐藏在历史(lìshǐ)沙砾中一千多年的楼兰古城,这一“神迹”才重现于世。
斯文·赫定回到欧洲,向全世界公布了罗布荒原上的(de)“沙埋文明”,轰动一时。神秘的“楼兰(lóulán)”是(shì)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成就之一,而楼兰古国所在(suǒzài)的这一片罗布荒原,成为了世界探险家趋之若鹜的神秘地带。
斯文·赫定曾在他那部著名的《亚洲腹地探险8年》一书中写道:“罗布泊使我惊讶,它像座仙湖(xiānhú),水面像镜子一样,在和煦的阳光(yángguāng)下,我乘舟而行,如(rú)神仙一般。”
作为此地最大的(de)沙漠咸湖,罗布泊也因此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。
上世纪初叶,罗布泊的“游移之谜(zhīmí)”曾引起世界学术界的极大争论。
最早(zuìzǎo)到新疆(xīnjiāng)考察的中外科学家们曾对罗布泊(luóbùpō)的确切位置争论不休,斯文·赫定认为罗布泊存在南北湖区,由于(yóuyú)入湖河水带有大量泥沙,沉积后抬高了湖底,原来的湖水就自然向另一处更低的地方流去,又过许多年,抬高的湖底会由于风蚀再次降低,湖水再度回流,这个周期为1510年,所以(suǒyǐ),他认为罗布泊是一个在沙漠中不断游移的湖。
斯文·赫定这(zhè)一学说,在(zài)当时曾得到(dédào)了世界普遍认可。“游移之谜”给罗布泊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,这片幽灵般的湖泊,再一次引起了全世界探险家的极大兴趣。
1927年,中国科学家第一次靠近(kàojìn)了这片“幽灵湖泊”。斯文·赫定在筹备第六次中亚考察时,决定由中瑞两国共同(gòngtóng)组成一个(yígè)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。时任北京大学教务长的知名学者徐炳旭(xúbǐngxù)担任中方团长,团中尽数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专家,如地质与古生物学家丁道衡、考古学家黄文弼、地理学家(dìlǐxuéjiā)陈宗器等。
这次考察从1927年持续到1933年,考察队先后在罗布泊、吐鲁番和塔里木盆地(tǎlǐmùpéndì)进行考古调查(diàochá)和部分试掘,撰写了《罗布淖尔考古记(jì)》、《吐鲁番考古记》、《塔里木盆地考古记》等,在国内出版,引起很大反响(fǎnxiǎng)。
此后的(de)很长一段时间,罗布泊的研究湮灭于连年战火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9年,罗布荒原终于又(yòu)迎来了一支新的科学考察队。
从1956年到1959年,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(zōnghé)考察队对塔里木下游和罗布泊地区(dìqū)进行了新中国成立后最大规模的一次综合考察,当时,队员们是乘着舟进入(jìnrù)罗布泊的。
夏训诚因被分在北疆(běijiāng)组考察,遗憾地与当时(dāngshí)尚未干涸的(de)罗布泊失之交臂。他说,那次考察留下了人类在罗布泊荡舟的最后记录,“由于1952年在拉依河筑坝,使塔里木河和孔雀河(kǒngquèhé)彻底分流,孔雀河下泄的河水逐渐断绝,罗布泊在上世纪(shìjì)70年代初全部干涸了,终结了它作为一个湖泊的历史。”
那次考察后不久,罗布泊被定为核试验场,从此成为军事禁区。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,任何与核试验无关的人都不得进入(jìnrù)这个地区(dìqū)。
彭加木也没有参加(cānjiā)那次考察。那时他正在上海(shànghǎi)的医院中,与恶性肿瘤、癌细胞搏斗着。
“彭加木”这个名字,也刚刚出现(chūxiàn)不久。
1947年,22岁的广东番禺青年彭家睦从中央大学(1949年更名(gēngmíng)南京大学)农学院毕业,到(dào)北京大学农学院任教,专攻农业化学。1949年,他被分配(fēnpèi)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。
1956年初,中央发出了“向(xiàng)科学进军”的号召,正当(zhèngdāng)此时,彭家睦迎来了一个对他个人发展千载难逢的机会。
科学院的领导研究决定,派年轻的彭家睦到莫斯科(mòsīkē)去(qù)学习一项新的技术——核磁共振,办理完出国手续即刻便要动身。
能够去苏联学习,无疑是一个好机会,彭家睦自然是高兴极了,但是他(tā)马上又(yòu)陷入了两难的选择中。
就在这个当口,中国科学院为了开发祖国边疆的丰富资源,组织了综合考察委员会。这个委员会此时正在“招兵买马(zhāobīngmǎimǎ)”,吸收各方面(fāngmiàn)科技人才,准备(zhǔnbèi)组成若干小组,分赴祖国边疆各地进行实地考察。
究竟是去国外留学还是去边疆考察,31岁的彭家(péngjiā)睦面临重要的人生选择,经过反复(fǎnfù)考虑后,他选择了后者。
彭家睦曾经亲笔写下作出这一选择的(de)(de)原因:“我必须在出国和到边疆之间立刻做出选择,我考虑的结果,认为出国学习的任务虽然重要,但可以由别的同志来完成,别的同志也乐于去(qù)干(gàn),为了让科学在祖国遍地开花,作为一个共产党员,应当选择到最艰苦的地方去。”
在同样(tóngyàng)毕业于南京大学的(de)夏训诚看来,彭家睦当年的选择着实令人敬佩:“上海的科研条件自然(zìrán)比边疆要好得多,而且他当时在植物学领域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,但是为了边疆的科研,他甘愿(gānyuàn)做铺路石子。”
1956年3月, 彭家睦的申请正式得到了批准,他如愿以偿地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(shēngwùhuàxué)研究所调到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工作(gōngzuò),当时的职务是助理(zhùlǐ)研究员。
此时,他的户口也从上海迁到了北京(běijīng)。在(zài)迁户口时,彭家睦打(dǎ)了一个改名报告,把“彭家睦”改为了“彭加木”。从此,他一直用“彭加木”这个名字。
实际上,在迁户口之前,他就已经在使用“彭加木”的名字了。为了争取参加中(zhōng)国边疆科考,彭加木直接写信给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。他在信中(xìnzhōng)写道:“我具有从荒野中踏出一条(yītiáo)道路(dàolù)的勇气。”在信的末尾,署名并不是“彭家睦”,而是“彭加木”。
从“彭家睦”到“彭加木”,其实是他表示“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”的决心。彭加木认为“家睦”只是希望家庭和睦,着眼于(zhuóyǎnyú)小家(xiǎojiā),太狭隘(xiáài)了;他要跳出小家庭,为边疆“添草加木”。
那一年的秋天,彭加木第一次来到(láidào)乌鲁木齐。当时(dāngshí)新疆的科研事业只是有了一点点萌芽,而在生物化学研究方面几乎是一个空白。一到新疆,彭加木就帮助当地筹建了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。然而(ránér),这个豪情万丈的垦荒者,却突然遭受了一个重大打击(dǎjī)。
1957年初,彭加木突然被查出患有纵隔障恶性肿瘤,返回上海治疗。以当时的医疗条件,医生们根据(gēnjù)有限的医学文献和病例判断(pànduàn),彭加木最多只能(zhǐnéng)活两年。
祸不单行的是,在住院期间,彭加木又(yòu)被查出还患有另一种恶性肿瘤——网状细胞(xìbāo)淋巴瘤,患这种病一般只能活几个月。
等于是被判了死刑的彭加木却没有(méiyǒu)被病魔打倒(dǎdǎo),一年以后,他竟然奇迹般地康复了。虽然医生严令禁止他离开上海(shànghǎi),但是彭加木刚一出院就接二连三地要求“放虎归山”,回到新疆去工作。
1958年的春天,一个险些被癌症夺去生命的人,又踏上了西行(xīxíng)的旅程,彭加木与罗布泊也从此正式(zhèngshì)结缘。
彭加木在新疆工作期间,一共有过四次对(duì)新疆地区的大规模考察(kǎochá)。这些考察包括人文、地理、生物、矿产资源、文物古籍、风土民情等。
1959年,彭加木(péngjiāmù)曾到过罗布泊北部地区,采集过土壤标本。经过化验,他发现此地土壤中的(de)钾含量(hánliàng)非常高。1964年,他对流入罗布泊的孔雀河、塔里木河、车尔臣河等河流进行了综合考察。参与这次考察的共有四个人(rén),由彭加木带队(dàiduì),此外还有新疆化学所的两名科研工作者和一名司机。考察从9月上旬到10月下旬,历时40多天,行程近5000公里(gōnglǐ)。
在(zài)对流入罗布泊的(de)几条河的钾含量作了初步分析后,彭加木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——罗布泊极有可能蕴藏巨大储量的钾盐。
钾盐是农用钾肥的生产原料,在我国属大宗紧缺(jǐnquē)矿种,中国(zhōngguó)境内可溶性钾盐资源严重不足,需要大量进口。
彭加木同时判断,在罗布泊的(de)盐层中,还含有宝贵的原料,比如制造(zhìzào)飞机所需的镁,稀有金属锂(lǐ)等。另外,那里还可能有重水资源。重水是重要的中子减速器,无论是建造原子能反应堆还是制造原子弹都会用到它(tā),此外,它还是制造氢弹的原料,属于重要的战略资源。
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,我国(wǒguó)在钾盐勘查方面投入(tóurù)大量(dàliàng)的人力和经费,除了在柴达木盆地取得重大突破外,其它(qítā)地区成果甚微,以致出现了中国“无钾论”的看法。中国是否能再找到大型钾盐矿床,一直是科学界关注的焦点。
那次考察中,在塔里木河下游,彭加木发现河水(héshuǐ)的(de)钾含量在逐渐增加。他根据气象资料推算出河水的流量,并从河水的流量数据(shùjù)推算出河流搬运钾元素的大约值,由此(yóucǐ)估算出罗布泊每年会积聚约75万吨钾,可能还含有其他稀有金属和重水等资源。
夏训诚说,彭加木是(shì)第一个提出罗布泊有钾盐矿(kuàng)的(de)人。如果罗布泊果真富集钾盐矿,这里就不再是人迹罕至的荒漠,而是一个巨大的“聚宝盆”。
在新疆进行这一次考察时,彭加木39岁,在罗布泊寻找钾盐矿成为了他对这片神秘(shénmì)区域最初的研究目标。遗憾(yíhàn)的是,由于“文革”的影响,他对罗布泊的研究计划(jìhuà)也不得不搁浅了十余年。
“地球之耳”的(de)神秘大门对彭加木再次打开的时候,他已经54岁了(le)。对一个科学家来说,这个年龄还(hái)算年轻。然而,重新走进这道大门仅仅一年时间,彭加木的生命戛然而止。
1979年的(de)冬天,刚刚率领科学考察队从(cóng)天山最高峰——托木尔峰归来的夏训诚,突然接到新疆考古所副所长穆舜英打来的电话。
穆舜英在电话中说,由中日联合组成的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即将(jíjiāng)来新疆,在罗布泊(luóbùpō)附近进行(jìnxíng)实地拍摄。夏训诚被聘请为“顾问”,要组成一个“先遣队”进入罗布泊打个前站。
罗布泊在上世纪60年代(niándài)被列为军事禁区,又因“文革”的关系,此地的科学考察一直处于停滞状态。对夏(duìxià)训诚来说,能够再次进入罗布泊就像是“圆梦”一样,兴奋之余,他突然想到(xiǎngdào)了老朋友彭加木。
致力于沙漠治理的夏训诚从上(shàng)世纪50年代起就一直在新疆进行考察和研究,因工作关系与彭加木(péngjiāmù)结识多年,“我知道他一直想去罗布泊找钾盐,这个机会千载难逢(qiānzǎinánféng)。”夏训诚说。
于是,他(tā)把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告诉了(le)彭加木,彭加木当时竟高兴得跳了起来,连说“太好了(tàihǎole)”。夏训诚现在仍然记得,彭加木当时像孩子一样握着他的手,一直恳求他帮忙,与有关单位(dānwèi)联系参加这次考察。
夏训诚回忆,当时联系的过程颇为复杂,罗布泊毕竟是几十年的军事禁区。“据我了解,《丝绸之路(sīchóuzhīlù)》摄制组此行进入(jìnrù)罗布泊,是邓小平(dèngxiǎopíng)同志亲自(qīnzì)批准的。”最终,执着的彭加木还是得到了这次进入罗布泊的机会。
“先遣队”不是一个(yígè)严格(yángé)的科学考察的组织,但是每(měi)一个队员都有自己心里的“小算盘”,作为地理工作者,夏训诚关注罗布泊的自然环境变迁情况;而对于彭加木来说,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延续上世纪60年代未完成的考察计划,在罗布泊寻找钾盐(jiǎyán)。
这是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,罗布泊(luóbùpō)地(dì)区第一次向非军事人员开放。20余天的时间(shíjiān)里,6辆吉普车组成的车队穿过了沉寂的荒原,穿过楼兰古城和白龙堆雅丹,在完成了几次横向与纵向穿插罗布泊西部的考察后,“先遣队”成功地回到了乌鲁木齐的基地(jīdì)。
在离开基地的前一天(qiányītiān),彭加木向夏训诚提议,由他俩(tāliǎ)牵头,上书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建议正式组建考察队,对罗布泊进行(jìnxíng)全面的综合考察。
彭加木此时提出考察计划,已(yǐ)不仅仅(bùjǐnjǐn)为了他寻找已久的钾盐矿。一个多世纪以来(yǐlái),俄国人、瑞典人、日本人一次一次来到罗布泊(luóbùpō)考察、探险,写出了许多关于罗布泊的文章,以至于国外竟有一种言论:“罗布泊在中国,而罗布泊的研究在外国”。彭加木向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表示,要夺回中国科学家在罗布泊的发言权。
几天以后,彭加木正式调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,这无疑对(duì)组建罗布泊考察队起到了积极的(de)作用。
1980年初(niánchū),通过各方面的努力,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(fēnyuàn)正式下达了成立(chénglì)罗布泊科学考察队的文件,并决定由彭加木担任队长,夏训诚担任副队长。
彭加木心中多年的夙愿,即将(jíjiāng)达成。
根据计划(jìhuà),这次对罗布泊的综合考察分三次进行。1980年的第一次考察主要(zhǔyào)是路线考察,时间定在1980年的5、6月间,第二年再进行后两次(liǎngcì)考察。
“第一次考察之所以(zhīsuǒyǐ)定在(zài)这个月份,是因为这时正是沙漠荒原风沙季节和酷热季节的‘空档’。”夏训诚说。但是他认为当时的计划并(bìng)不周全,“我们当时不知道,实际上罗布泊地区(dìqū)并没有这种‘空档’,或者说很短促。”
在制定计划的同时,考察队正式开始“招兵买马”。夏训诚主持组建队伍的工作,他从新疆分院的好几个部门抽调了6名专业(zhuānyè)人员和3名司机、一名后勤(hòuqín),这十位同志组成(zǔchéng)了一支罗布泊科学考察队。
5月3日,由彭加木率队,罗布泊(luóbùpō)科学考察队从乌鲁木齐出发,正式向罗布泊进发了(le)。因为在出发前突然接到去美国考察的通知,夏训诚遗憾地(dì)错过了参加第一次路线考察的机会。
夏训诚直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,建议组建考察队时,彭加木曾悲愤地说(dìshuō):“我不希望在罗布泊全是外国人(wàiguórén)留下的足迹,作为一个中国人,我就觉得应该把自己的骨头(gútou)埋在罗布泊,使它的土壤多一点(duōyìdiǎn)中国的有机质!”
这不是一句玩笑,而是彭加木(péngjiāmù)的真实想法。如果说科学探索总(zǒng)需要牺牲,他是在进入罗布泊之前,就已经作好了牺牲准备的。
夏训诚万万没有想到,仅仅一个多月以后,彭加木的话(dehuà)一语成谶。
作为对罗布泊的(de)第一次深入性考察,彭加木的计划是十分大胆的。
他打算率队从北至南,纵穿(zòngchuān)罗布泊。在他看来,只有纵穿罗布泊,才能弄清这个神秘之地(zhīdì)的真实面目。
但是(dànshì),第一次纵穿并未成功。彭加木(péngjiāmù)在日记中写道:“我们在5月9日开始进入湖区,有(yǒu)一个七人(qīrén)探路小分队,自北往南纵贯罗布泊湖底。湖表面已没有水,有些地面松软陷车,有些地面则比较平整。汽车车胎由于锋利的盐晶块切割,损耗过大,无法继续前进。”
那天晚上,考察队只能原地宿营。因为当时(dāngshí)所带的汽油和水(shuǐ)都消耗了不少,彭加木只得决定原路返回,重新补充油、水之后再度前进。
湖底的(de)盐晶块是前进的极大阻碍,最终用来给考察队(kǎocháduì)开路的,竟然是队员们手中十几(shíjǐ)磅重的大铁锤。这个方法也是彭加木提出(tíchū)的,最初遭到队员们的一致反对,大家认为在罗布泊湖底用铁锤人工开路简直是天方夜谭。
事实证明(shìshízhèngmíng),彭加木的意见是正确的。5月30日,考察队重新出发,又一次到了这个地区,大家拿着铁锤下车,一锤一锤地把车轮前的盐晶块(yánjīngkuài)砸碎。汽车(qìchē)颠簸前行,直到他们找到了古河道的入湖口,路(lù)才一下子平顺了起来,盐晶块对车行的阻碍得以解除。
汽车沿着古河道走了两天,终于完成了纵贯罗布泊的计划。沿途(yántú),考察队进行了简单的地质勘探,彭加木凿开盐壳,从下面瓦蓝色(lánsè)的沙层中取出一个水样(shuǐyàng),兴奋地对大家说:“这里可能有‘重水’!”能够在地域广阔的罗布泊找到重水资源,这无疑(wúyí)是(shì)对中国核物理工业发展的一个巨大贡献。
彭加木曾这样评价此次纵穿罗布泊的(de)经历(jīnglì):“此次胜利的穿越盐壳地带,自北而南纵贯罗布泊干涸湖底(húdǐ)成功,是一个很大的收获,这是前所未有的,对罗布泊洼地中心区域已经有了一些了解,可算(kěsuàn)得是敲开了罗布泊的大门。”
考察队在6月5日到达(dàodá)了考察的最后一站——米兰农场。
进入米兰(mǐlán)农场(nóngchǎng)以后,考察队的队员们如同卸下了千斤重担。按原定的方案,在米兰农场休息几天后考察队就可以启程回乌鲁木齐了。
就在此时,彭加木突然向队员们提出了(le)“东进计划”。
这次考察原计划到7月3日结束,还有近一个月时间。彭加木建议(jiànyì)暂不回乌鲁木齐,利用剩下的这些时间一鼓作气(yīgǔzuòqì)完成对(duì)整个罗布泊地区的考察。
1979年冬天,彭加木作为纪录片《丝绸之路》的“先遣队”成员之一,曾完成了对罗布泊西部的考察(kǎochá),这次,考察队又从罗布泊的中部纵穿(zòngchuān)而过,他计划在余下一个月(yígèyuè)的时间里,沿罗布泊东部北上,穿过疏流河(liúhé)直至敦煌,完成对罗布泊地区的全面考察,最后再(zài)回乌鲁木齐。
虽然队员们已经非常疲惫,但最终大家还是(háishì)决定采纳彭加木的建议。
彭加木通过电报向中科院新疆分院(fēnyuàn)汇报请求批准。新疆分院接到电报后,经研究同意他们的计划,但(dàn)一再嘱咐(yīzàizhǔfù),一定要注意安全,有情况及时与基地联系。
在准备出发,装(zhuāng)汽油和水的时候,彭加木提议可以多装一桶汽油,少装一桶水。原因是从地图上看,到了库木库都克这个地方(dìfāng)有水井(shuǐjǐng),可以在这个地方补充水源。根据路程(lùchéng)计算,到库木库都克只有400多公里,最多两天即可赶到。
然而,在这一段路上,考察队(kǎocháduì)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麻烦。
6月11日,考察队一早从米兰出发,一直赶路到天黑。十几个小时,车子只走了(le)58公里(lǐ),还不到计划行程的(de)一半。一路都是松软的沙石地,三辆车不是这辆陷进了泥坑,就是那辆困(kùn)在了沙窝子,有时候几个小时才能把一辆车从泥坑里弄出来,此后的几天里也都是如此,结果,本来预计两天的路程考察队走了整整(zhěngzhěng)6天。
6月16日下午6时左右,考察队终于赶到(gǎndào)了库木库都克,此时大家都已是筋疲力尽,却不得不再次外出——由于行程(xíngchéng)被耽搁,出发时带的汽油和水此时都快要消耗(xiāohào)殆尽了。
“库木库都克”是维吾尔语(wéiwúěryǔ)“沙井”的意思。从考察队带的那张地图看,这里确实标有水井。考察队支好帐篷,休息了一会儿(yīhuìer),便立刻出发去找水(zhǎoshuǐ)。
让彭加木和队员们大为失望的是,从下午找到晚上,这片茫茫的沙漠中根本没有水(shuǐ)井的踪影。眼下,所剩的汽油只能供三辆(sānliàng)车行驶几十公里;水,则只剩下一汽油桶,且(qiě)已变质,难以饮用。
没有水和汽油,考察队员们即刻就面临生命危险,几乎陷入绝境的(de)考察队决定向部队紧急求助(qiúzhù)。
6月16日晚上10时10分,彭加木亲自起草了发给部队的告急电报:“我们已到(dào)达了库木库都克以西大约十公里。我们缺油和水(shuǐ),请求紧急(jǐnjí)支援油、水各500公斤,现有的水只能维持到18日。”
电报发出后(hòu),正在大家焦急等待回复的时候(shíhòu),彭加木提出了新的建议。
一向节俭的彭加木认为,用直升机运水(yùnshuǐ)太贵了(le)。直升机飞行一小时,在那个年代要花2000多块钱,从驻军基地到宿营地,来回(láihuí)要飞好几个小时。他建议大家自力更生,尽量自己找水。
不久前,他和别人闲聊中听说,年初的时候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曾经在“八一泉(quán)”加过(jiāguò)水。“八一泉”位于疏流河故道北岸,在库木库都克东北约30公里处(chù)。
所以,彭加木建议开车(kāichē)再(zài)往东面去找一次水井,但是这个建议遭到了(le)队员们的全体反对。大家计算了一下,这一路线要用掉(diào)大概半桶汽油,大家一致认为不能再消耗本已不多的汽油,应该等与部队联系上以后,再作打算。
第二天上午(shàngwǔ)11点半,考察队收到了部队发来的电报:“飞机18日到库木库都克送水(shuǐ),你们不要动,原地待命。”
接到电报(diànbào),大家都很兴奋。队员汪文先想把这一喜讯告诉(gàosù)彭加木,他拿着电文走出帐篷,却没有看到彭加木的身影。
他以为彭加木只是去附近解手了,于是又回帐篷(zhàngpéng)等待。一个小时后还未见彭加木回来,大家方(fāng)感觉有些不妙了。
此时,司机(sījī)王万轩(wángwànxuān)走出帐篷,到汽车上去取衣服。他突然发现右边的座位上有一张摊开的地图。这张地图是全队唯一一张地形图,彭加木一路上一直坐在这个(zhègè)位置,他是从不把这张地图随意丢放的。
王万轩把地图(dìtú)拿起收好,突见地图下面有一张纸条,上面写道:
“我往东去找水井(shuǐjǐng)。彭,17/6 10:30”
卫星(wèixīng)拍下的“地球之耳”罗布泊。
罗布泊的(de)神秘之处,并不仅仅在于它奇特(qítè)的地理构造,更源于它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湮灭在漫漫黄沙下的历史传说。
罗布泊历史上最繁华的一个时期,是在“楼兰(lóulán)王国”兴盛之时。楼兰古城地处罗布泊的西北侧,这里曾经(céngjīng)是丝绸之路南支的咽喉门户。
楼兰于公元前176年以前(yǐqián)建国、公元630年消亡,历时800多年。随着(suízhe)楼兰国的消亡,这里渐渐成为人迹罕至之地,丝绸之路的故道不复存在,罗布荒原逐渐被人们所遗忘(yíwàng)。
直到1900年3月,瑞典探险家斯文(sīwén)·赫定探险队沿着干枯的孔雀河左河床来到罗布荒原,意外(yìwài)地发现了隐藏在历史(lìshǐ)沙砾中一千多年的楼兰古城,这一“神迹”才重现于世。
斯文·赫定回到欧洲,向全世界公布了罗布荒原上的(de)“沙埋文明”,轰动一时。神秘的“楼兰(lóulán)”是(shì)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成就之一,而楼兰古国所在(suǒzài)的这一片罗布荒原,成为了世界探险家趋之若鹜的神秘地带。
斯文·赫定曾在他那部著名的《亚洲腹地探险8年》一书中写道:“罗布泊使我惊讶,它像座仙湖(xiānhú),水面像镜子一样,在和煦的阳光(yángguāng)下,我乘舟而行,如(rú)神仙一般。”
作为此地最大的(de)沙漠咸湖,罗布泊也因此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。
上世纪初叶,罗布泊的“游移之谜(zhīmí)”曾引起世界学术界的极大争论。
最早(zuìzǎo)到新疆(xīnjiāng)考察的中外科学家们曾对罗布泊(luóbùpō)的确切位置争论不休,斯文·赫定认为罗布泊存在南北湖区,由于(yóuyú)入湖河水带有大量泥沙,沉积后抬高了湖底,原来的湖水就自然向另一处更低的地方流去,又过许多年,抬高的湖底会由于风蚀再次降低,湖水再度回流,这个周期为1510年,所以(suǒyǐ),他认为罗布泊是一个在沙漠中不断游移的湖。
斯文·赫定这(zhè)一学说,在(zài)当时曾得到(dédào)了世界普遍认可。“游移之谜”给罗布泊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,这片幽灵般的湖泊,再一次引起了全世界探险家的极大兴趣。
1927年,中国科学家第一次靠近(kàojìn)了这片“幽灵湖泊”。斯文·赫定在筹备第六次中亚考察时,决定由中瑞两国共同(gòngtóng)组成一个(yígè)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。时任北京大学教务长的知名学者徐炳旭(xúbǐngxù)担任中方团长,团中尽数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专家,如地质与古生物学家丁道衡、考古学家黄文弼、地理学家(dìlǐxuéjiā)陈宗器等。
这次考察从1927年持续到1933年,考察队先后在罗布泊、吐鲁番和塔里木盆地(tǎlǐmùpéndì)进行考古调查(diàochá)和部分试掘,撰写了《罗布淖尔考古记(jì)》、《吐鲁番考古记》、《塔里木盆地考古记》等,在国内出版,引起很大反响(fǎnxiǎng)。
此后的(de)很长一段时间,罗布泊的研究湮灭于连年战火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9年,罗布荒原终于又(yòu)迎来了一支新的科学考察队。
从1956年到1959年,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(zōnghé)考察队对塔里木下游和罗布泊地区(dìqū)进行了新中国成立后最大规模的一次综合考察,当时,队员们是乘着舟进入(jìnrù)罗布泊的。
夏训诚因被分在北疆(běijiāng)组考察,遗憾地与当时(dāngshí)尚未干涸的(de)罗布泊失之交臂。他说,那次考察留下了人类在罗布泊荡舟的最后记录,“由于1952年在拉依河筑坝,使塔里木河和孔雀河(kǒngquèhé)彻底分流,孔雀河下泄的河水逐渐断绝,罗布泊在上世纪(shìjì)70年代初全部干涸了,终结了它作为一个湖泊的历史。”
那次考察后不久,罗布泊被定为核试验场,从此成为军事禁区。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,任何与核试验无关的人都不得进入(jìnrù)这个地区(dìqū)。
彭加木也没有参加(cānjiā)那次考察。那时他正在上海(shànghǎi)的医院中,与恶性肿瘤、癌细胞搏斗着。
“彭加木”这个名字,也刚刚出现(chūxiàn)不久。
1947年,22岁的广东番禺青年彭家睦从中央大学(1949年更名(gēngmíng)南京大学)农学院毕业,到(dào)北京大学农学院任教,专攻农业化学。1949年,他被分配(fēnpèi)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。
1956年初,中央发出了“向(xiàng)科学进军”的号召,正当(zhèngdāng)此时,彭家睦迎来了一个对他个人发展千载难逢的机会。
科学院的领导研究决定,派年轻的彭家睦到莫斯科(mòsīkē)去(qù)学习一项新的技术——核磁共振,办理完出国手续即刻便要动身。
能够去苏联学习,无疑是一个好机会,彭家睦自然是高兴极了,但是他(tā)马上又(yòu)陷入了两难的选择中。
就在这个当口,中国科学院为了开发祖国边疆的丰富资源,组织了综合考察委员会。这个委员会此时正在“招兵买马(zhāobīngmǎimǎ)”,吸收各方面(fāngmiàn)科技人才,准备(zhǔnbèi)组成若干小组,分赴祖国边疆各地进行实地考察。
究竟是去国外留学还是去边疆考察,31岁的彭家(péngjiā)睦面临重要的人生选择,经过反复(fǎnfù)考虑后,他选择了后者。
彭家睦曾经亲笔写下作出这一选择的(de)(de)原因:“我必须在出国和到边疆之间立刻做出选择,我考虑的结果,认为出国学习的任务虽然重要,但可以由别的同志来完成,别的同志也乐于去(qù)干(gàn),为了让科学在祖国遍地开花,作为一个共产党员,应当选择到最艰苦的地方去。”
在同样(tóngyàng)毕业于南京大学的(de)夏训诚看来,彭家睦当年的选择着实令人敬佩:“上海的科研条件自然(zìrán)比边疆要好得多,而且他当时在植物学领域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,但是为了边疆的科研,他甘愿(gānyuàn)做铺路石子。”
1956年3月, 彭家睦的申请正式得到了批准,他如愿以偿地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(shēngwùhuàxué)研究所调到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工作(gōngzuò),当时的职务是助理(zhùlǐ)研究员。
此时,他的户口也从上海迁到了北京(běijīng)。在(zài)迁户口时,彭家睦打(dǎ)了一个改名报告,把“彭家睦”改为了“彭加木”。从此,他一直用“彭加木”这个名字。
实际上,在迁户口之前,他就已经在使用“彭加木”的名字了。为了争取参加中(zhōng)国边疆科考,彭加木直接写信给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。他在信中(xìnzhōng)写道:“我具有从荒野中踏出一条(yītiáo)道路(dàolù)的勇气。”在信的末尾,署名并不是“彭家睦”,而是“彭加木”。
从“彭家睦”到“彭加木”,其实是他表示“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”的决心。彭加木认为“家睦”只是希望家庭和睦,着眼于(zhuóyǎnyú)小家(xiǎojiā),太狭隘(xiáài)了;他要跳出小家庭,为边疆“添草加木”。
那一年的秋天,彭加木第一次来到(láidào)乌鲁木齐。当时(dāngshí)新疆的科研事业只是有了一点点萌芽,而在生物化学研究方面几乎是一个空白。一到新疆,彭加木就帮助当地筹建了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。然而(ránér),这个豪情万丈的垦荒者,却突然遭受了一个重大打击(dǎjī)。
1957年初,彭加木突然被查出患有纵隔障恶性肿瘤,返回上海治疗。以当时的医疗条件,医生们根据(gēnjù)有限的医学文献和病例判断(pànduàn),彭加木最多只能(zhǐnéng)活两年。
祸不单行的是,在住院期间,彭加木又(yòu)被查出还患有另一种恶性肿瘤——网状细胞(xìbāo)淋巴瘤,患这种病一般只能活几个月。
等于是被判了死刑的彭加木却没有(méiyǒu)被病魔打倒(dǎdǎo),一年以后,他竟然奇迹般地康复了。虽然医生严令禁止他离开上海(shànghǎi),但是彭加木刚一出院就接二连三地要求“放虎归山”,回到新疆去工作。
1958年的春天,一个险些被癌症夺去生命的人,又踏上了西行(xīxíng)的旅程,彭加木与罗布泊也从此正式(zhèngshì)结缘。
彭加木在新疆工作期间,一共有过四次对(duì)新疆地区的大规模考察(kǎochá)。这些考察包括人文、地理、生物、矿产资源、文物古籍、风土民情等。
1959年,彭加木(péngjiāmù)曾到过罗布泊北部地区,采集过土壤标本。经过化验,他发现此地土壤中的(de)钾含量(hánliàng)非常高。1964年,他对流入罗布泊的孔雀河、塔里木河、车尔臣河等河流进行了综合考察。参与这次考察的共有四个人(rén),由彭加木带队(dàiduì),此外还有新疆化学所的两名科研工作者和一名司机。考察从9月上旬到10月下旬,历时40多天,行程近5000公里(gōnglǐ)。
在(zài)对流入罗布泊的(de)几条河的钾含量作了初步分析后,彭加木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——罗布泊极有可能蕴藏巨大储量的钾盐。
钾盐是农用钾肥的生产原料,在我国属大宗紧缺(jǐnquē)矿种,中国(zhōngguó)境内可溶性钾盐资源严重不足,需要大量进口。
彭加木同时判断,在罗布泊的(de)盐层中,还含有宝贵的原料,比如制造(zhìzào)飞机所需的镁,稀有金属锂(lǐ)等。另外,那里还可能有重水资源。重水是重要的中子减速器,无论是建造原子能反应堆还是制造原子弹都会用到它(tā),此外,它还是制造氢弹的原料,属于重要的战略资源。
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,我国(wǒguó)在钾盐勘查方面投入(tóurù)大量(dàliàng)的人力和经费,除了在柴达木盆地取得重大突破外,其它(qítā)地区成果甚微,以致出现了中国“无钾论”的看法。中国是否能再找到大型钾盐矿床,一直是科学界关注的焦点。
那次考察中,在塔里木河下游,彭加木发现河水(héshuǐ)的(de)钾含量在逐渐增加。他根据气象资料推算出河水的流量,并从河水的流量数据(shùjù)推算出河流搬运钾元素的大约值,由此(yóucǐ)估算出罗布泊每年会积聚约75万吨钾,可能还含有其他稀有金属和重水等资源。
夏训诚说,彭加木是(shì)第一个提出罗布泊有钾盐矿(kuàng)的(de)人。如果罗布泊果真富集钾盐矿,这里就不再是人迹罕至的荒漠,而是一个巨大的“聚宝盆”。
在新疆进行这一次考察时,彭加木39岁,在罗布泊寻找钾盐矿成为了他对这片神秘(shénmì)区域最初的研究目标。遗憾(yíhàn)的是,由于“文革”的影响,他对罗布泊的研究计划(jìhuà)也不得不搁浅了十余年。
“地球之耳”的(de)神秘大门对彭加木再次打开的时候,他已经54岁了(le)。对一个科学家来说,这个年龄还(hái)算年轻。然而,重新走进这道大门仅仅一年时间,彭加木的生命戛然而止。
1979年的(de)冬天,刚刚率领科学考察队从(cóng)天山最高峰——托木尔峰归来的夏训诚,突然接到新疆考古所副所长穆舜英打来的电话。
穆舜英在电话中说,由中日联合组成的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即将(jíjiāng)来新疆,在罗布泊(luóbùpō)附近进行(jìnxíng)实地拍摄。夏训诚被聘请为“顾问”,要组成一个“先遣队”进入罗布泊打个前站。
罗布泊在上世纪60年代(niándài)被列为军事禁区,又因“文革”的关系,此地的科学考察一直处于停滞状态。对夏(duìxià)训诚来说,能够再次进入罗布泊就像是“圆梦”一样,兴奋之余,他突然想到(xiǎngdào)了老朋友彭加木。
致力于沙漠治理的夏训诚从上(shàng)世纪50年代起就一直在新疆进行考察和研究,因工作关系与彭加木(péngjiāmù)结识多年,“我知道他一直想去罗布泊找钾盐,这个机会千载难逢(qiānzǎinánféng)。”夏训诚说。
于是,他(tā)把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告诉了(le)彭加木,彭加木当时竟高兴得跳了起来,连说“太好了(tàihǎole)”。夏训诚现在仍然记得,彭加木当时像孩子一样握着他的手,一直恳求他帮忙,与有关单位(dānwèi)联系参加这次考察。
夏训诚回忆,当时联系的过程颇为复杂,罗布泊毕竟是几十年的军事禁区。“据我了解,《丝绸之路(sīchóuzhīlù)》摄制组此行进入(jìnrù)罗布泊,是邓小平(dèngxiǎopíng)同志亲自(qīnzì)批准的。”最终,执着的彭加木还是得到了这次进入罗布泊的机会。
“先遣队”不是一个(yígè)严格(yángé)的科学考察的组织,但是每(měi)一个队员都有自己心里的“小算盘”,作为地理工作者,夏训诚关注罗布泊的自然环境变迁情况;而对于彭加木来说,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延续上世纪60年代未完成的考察计划,在罗布泊寻找钾盐(jiǎyán)。
这是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,罗布泊(luóbùpō)地(dì)区第一次向非军事人员开放。20余天的时间(shíjiān)里,6辆吉普车组成的车队穿过了沉寂的荒原,穿过楼兰古城和白龙堆雅丹,在完成了几次横向与纵向穿插罗布泊西部的考察后,“先遣队”成功地回到了乌鲁木齐的基地(jīdì)。
在离开基地的前一天(qiányītiān),彭加木向夏训诚提议,由他俩(tāliǎ)牵头,上书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建议正式组建考察队,对罗布泊进行(jìnxíng)全面的综合考察。
彭加木此时提出考察计划,已(yǐ)不仅仅(bùjǐnjǐn)为了他寻找已久的钾盐矿。一个多世纪以来(yǐlái),俄国人、瑞典人、日本人一次一次来到罗布泊(luóbùpō)考察、探险,写出了许多关于罗布泊的文章,以至于国外竟有一种言论:“罗布泊在中国,而罗布泊的研究在外国”。彭加木向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表示,要夺回中国科学家在罗布泊的发言权。
几天以后,彭加木正式调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,这无疑对(duì)组建罗布泊考察队起到了积极的(de)作用。
1980年初(niánchū),通过各方面的努力,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(fēnyuàn)正式下达了成立(chénglì)罗布泊科学考察队的文件,并决定由彭加木担任队长,夏训诚担任副队长。
彭加木心中多年的夙愿,即将(jíjiāng)达成。
根据计划(jìhuà),这次对罗布泊的综合考察分三次进行。1980年的第一次考察主要(zhǔyào)是路线考察,时间定在1980年的5、6月间,第二年再进行后两次(liǎngcì)考察。
“第一次考察之所以(zhīsuǒyǐ)定在(zài)这个月份,是因为这时正是沙漠荒原风沙季节和酷热季节的‘空档’。”夏训诚说。但是他认为当时的计划并(bìng)不周全,“我们当时不知道,实际上罗布泊地区(dìqū)并没有这种‘空档’,或者说很短促。”
在制定计划的同时,考察队正式开始“招兵买马”。夏训诚主持组建队伍的工作,他从新疆分院的好几个部门抽调了6名专业(zhuānyè)人员和3名司机、一名后勤(hòuqín),这十位同志组成(zǔchéng)了一支罗布泊科学考察队。
5月3日,由彭加木率队,罗布泊(luóbùpō)科学考察队从乌鲁木齐出发,正式向罗布泊进发了(le)。因为在出发前突然接到去美国考察的通知,夏训诚遗憾地(dì)错过了参加第一次路线考察的机会。
夏训诚直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,建议组建考察队时,彭加木曾悲愤地说(dìshuō):“我不希望在罗布泊全是外国人(wàiguórén)留下的足迹,作为一个中国人,我就觉得应该把自己的骨头(gútou)埋在罗布泊,使它的土壤多一点(duōyìdiǎn)中国的有机质!”
这不是一句玩笑,而是彭加木(péngjiāmù)的真实想法。如果说科学探索总(zǒng)需要牺牲,他是在进入罗布泊之前,就已经作好了牺牲准备的。
夏训诚万万没有想到,仅仅一个多月以后,彭加木的话(dehuà)一语成谶。
作为对罗布泊的(de)第一次深入性考察,彭加木的计划是十分大胆的。
他打算率队从北至南,纵穿(zòngchuān)罗布泊。在他看来,只有纵穿罗布泊,才能弄清这个神秘之地(zhīdì)的真实面目。
但是(dànshì),第一次纵穿并未成功。彭加木(péngjiāmù)在日记中写道:“我们在5月9日开始进入湖区,有(yǒu)一个七人(qīrén)探路小分队,自北往南纵贯罗布泊湖底。湖表面已没有水,有些地面松软陷车,有些地面则比较平整。汽车车胎由于锋利的盐晶块切割,损耗过大,无法继续前进。”
那天晚上,考察队只能原地宿营。因为当时(dāngshí)所带的汽油和水(shuǐ)都消耗了不少,彭加木只得决定原路返回,重新补充油、水之后再度前进。
湖底的(de)盐晶块是前进的极大阻碍,最终用来给考察队(kǎocháduì)开路的,竟然是队员们手中十几(shíjǐ)磅重的大铁锤。这个方法也是彭加木提出(tíchū)的,最初遭到队员们的一致反对,大家认为在罗布泊湖底用铁锤人工开路简直是天方夜谭。
事实证明(shìshízhèngmíng),彭加木的意见是正确的。5月30日,考察队重新出发,又一次到了这个地区,大家拿着铁锤下车,一锤一锤地把车轮前的盐晶块(yánjīngkuài)砸碎。汽车(qìchē)颠簸前行,直到他们找到了古河道的入湖口,路(lù)才一下子平顺了起来,盐晶块对车行的阻碍得以解除。
汽车沿着古河道走了两天,终于完成了纵贯罗布泊的计划。沿途(yántú),考察队进行了简单的地质勘探,彭加木凿开盐壳,从下面瓦蓝色(lánsè)的沙层中取出一个水样(shuǐyàng),兴奋地对大家说:“这里可能有‘重水’!”能够在地域广阔的罗布泊找到重水资源,这无疑(wúyí)是(shì)对中国核物理工业发展的一个巨大贡献。
彭加木曾这样评价此次纵穿罗布泊的(de)经历(jīnglì):“此次胜利的穿越盐壳地带,自北而南纵贯罗布泊干涸湖底(húdǐ)成功,是一个很大的收获,这是前所未有的,对罗布泊洼地中心区域已经有了一些了解,可算(kěsuàn)得是敲开了罗布泊的大门。”
考察队在6月5日到达(dàodá)了考察的最后一站——米兰农场。
进入米兰(mǐlán)农场(nóngchǎng)以后,考察队的队员们如同卸下了千斤重担。按原定的方案,在米兰农场休息几天后考察队就可以启程回乌鲁木齐了。
就在此时,彭加木突然向队员们提出了(le)“东进计划”。
这次考察原计划到7月3日结束,还有近一个月时间。彭加木建议(jiànyì)暂不回乌鲁木齐,利用剩下的这些时间一鼓作气(yīgǔzuòqì)完成对(duì)整个罗布泊地区的考察。
1979年冬天,彭加木作为纪录片《丝绸之路》的“先遣队”成员之一,曾完成了对罗布泊西部的考察(kǎochá),这次,考察队又从罗布泊的中部纵穿(zòngchuān)而过,他计划在余下一个月(yígèyuè)的时间里,沿罗布泊东部北上,穿过疏流河(liúhé)直至敦煌,完成对罗布泊地区的全面考察,最后再(zài)回乌鲁木齐。
虽然队员们已经非常疲惫,但最终大家还是(háishì)决定采纳彭加木的建议。
彭加木通过电报向中科院新疆分院(fēnyuàn)汇报请求批准。新疆分院接到电报后,经研究同意他们的计划,但(dàn)一再嘱咐(yīzàizhǔfù),一定要注意安全,有情况及时与基地联系。
在准备出发,装(zhuāng)汽油和水的时候,彭加木提议可以多装一桶汽油,少装一桶水。原因是从地图上看,到了库木库都克这个地方(dìfāng)有水井(shuǐjǐng),可以在这个地方补充水源。根据路程(lùchéng)计算,到库木库都克只有400多公里,最多两天即可赶到。
然而,在这一段路上,考察队(kǎocháduì)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麻烦。
6月11日,考察队一早从米兰出发,一直赶路到天黑。十几个小时,车子只走了(le)58公里(lǐ),还不到计划行程的(de)一半。一路都是松软的沙石地,三辆车不是这辆陷进了泥坑,就是那辆困(kùn)在了沙窝子,有时候几个小时才能把一辆车从泥坑里弄出来,此后的几天里也都是如此,结果,本来预计两天的路程考察队走了整整(zhěngzhěng)6天。
6月16日下午6时左右,考察队终于赶到(gǎndào)了库木库都克,此时大家都已是筋疲力尽,却不得不再次外出——由于行程(xíngchéng)被耽搁,出发时带的汽油和水此时都快要消耗(xiāohào)殆尽了。
“库木库都克”是维吾尔语(wéiwúěryǔ)“沙井”的意思。从考察队带的那张地图看,这里确实标有水井。考察队支好帐篷,休息了一会儿(yīhuìer),便立刻出发去找水(zhǎoshuǐ)。
让彭加木和队员们大为失望的是,从下午找到晚上,这片茫茫的沙漠中根本没有水(shuǐ)井的踪影。眼下,所剩的汽油只能供三辆(sānliàng)车行驶几十公里;水,则只剩下一汽油桶,且(qiě)已变质,难以饮用。
没有水和汽油,考察队员们即刻就面临生命危险,几乎陷入绝境的(de)考察队决定向部队紧急求助(qiúzhù)。
6月16日晚上10时10分,彭加木亲自起草了发给部队的告急电报:“我们已到(dào)达了库木库都克以西大约十公里。我们缺油和水(shuǐ),请求紧急(jǐnjí)支援油、水各500公斤,现有的水只能维持到18日。”
电报发出后(hòu),正在大家焦急等待回复的时候(shíhòu),彭加木提出了新的建议。
一向节俭的彭加木认为,用直升机运水(yùnshuǐ)太贵了(le)。直升机飞行一小时,在那个年代要花2000多块钱,从驻军基地到宿营地,来回(láihuí)要飞好几个小时。他建议大家自力更生,尽量自己找水。
不久前,他和别人闲聊中听说,年初的时候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曾经在“八一泉(quán)”加过(jiāguò)水。“八一泉”位于疏流河故道北岸,在库木库都克东北约30公里处(chù)。
所以,彭加木建议开车(kāichē)再(zài)往东面去找一次水井,但是这个建议遭到了(le)队员们的全体反对。大家计算了一下,这一路线要用掉(diào)大概半桶汽油,大家一致认为不能再消耗本已不多的汽油,应该等与部队联系上以后,再作打算。
第二天上午(shàngwǔ)11点半,考察队收到了部队发来的电报:“飞机18日到库木库都克送水(shuǐ),你们不要动,原地待命。”
接到电报(diànbào),大家都很兴奋。队员汪文先想把这一喜讯告诉(gàosù)彭加木,他拿着电文走出帐篷,却没有看到彭加木的身影。
他以为彭加木只是去附近解手了,于是又回帐篷(zhàngpéng)等待。一个小时后还未见彭加木回来,大家方(fāng)感觉有些不妙了。
此时,司机(sījī)王万轩(wángwànxuān)走出帐篷,到汽车上去取衣服。他突然发现右边的座位上有一张摊开的地图。这张地图是全队唯一一张地形图,彭加木一路上一直坐在这个(zhègè)位置,他是从不把这张地图随意丢放的。
王万轩把地图(dìtú)拿起收好,突见地图下面有一张纸条,上面写道:
“我往东去找水井(shuǐjǐng)。彭,17/6 10:30”
 彭加木失踪前留下的最后一张(yīzhāng)字条。
纸条显然是这天上午写下的,日(rì)期上的“17”日还是“16”日改写的,大概是彭加木曾经一时写错了日期。此时大家(dàjiā)才发现,彭加木的黄帆布包和(hé)那只能装两公斤水的水壶也不见了。
队员(duìyuán)们怎么也想不到,这张字条,竟是彭加木(péngjiāmù)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。
那天下午,所有队员出动寻找彭加木,他们按照(ànzhào)字条的指引向东寻,沿着彭加木那双42号翻毛皮靴在沙地中留下的脚印走了将近8公里,都不见他的踪影。脚印却(què)最终消失在盐(yán)壳地的边缘,搜寻(sōuxún)一下子失去了方向。
为了(le)跟部队及时电报联系,队员们只得在晚上10点回到了营地,大家在营地里燃起篝火,把吉普车开到最高处,向东方开亮(kāiliàng)了车前大灯,并每隔一小时(xiǎoshí)向空中发射一次信号弹。
队员们希望,彭加木可以循着亮光,找到(zhǎodào)营地的方向。
然而,彭加木消瘦的身影再也(zàiyě)没有出现在队员们的视线中。
6月18日凌晨两点,考察队(kǎocháduì)正式(zhèngshì)发出电报:彭加木走失,下落不明。
此时,距离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已经过去了16个小时。
18日中午,直升机载着500公斤水找到了考察队的露营地,队员们(men)获救了。第二天,部队又(yòu)给他们送来三桶汽油。但是,经过队员们持续十几个小时的寻找,没有任何(rènhé)结果。
搜寻中唯一的突破,是在一片岩石间(jiān)发现了一张椰子奶油糖的糖纸,旁边(pángbiān)还有人坐过的痕迹。队友们知道,这个牌子的奶油糖是彭加木随身携带的,但是沿着旁边的脚印(jiǎoyìn)追踪了几十公里后(hòu),脚印又在盐壳边缘消失了。
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于6月18日下午6点得到了彭加木失踪的消息。晚上12点,副院长(yuànzhǎng)陈善明带着两名干部,由两个司机轮流开车连夜往马兰基地(jīdì)(jīdì)赶。19日早晨7点一到基地,他就会同基地的几位领导(lǐngdǎo)组成了救援领导小组,组织对彭加木的救援工作。
一个大规模的寻找彭加木的战役拉开了(le)帷幕。
根据夏训诚的回忆,当年较大规模的寻找,一共有四次(sìcì)。
第一次寻找(xúnzhǎo)是在彭加木刚失踪时,6月18日到19日,队员们在宿营地周围(zhōuwéi)进行了搜寻。
第二次寻找是在6月(yuè)20日到26日,在收到(shōudào)呼救讯号后,当地部队和科考(kēkǎo)队员出动136人次,空军出动9架直升机、三架“安-2”型飞机,在出事地点东西50公里范围内进行地毯式低空搜寻。
第三次寻找是(shì)在7月(yuè)7日到8月2日,117人,48辆车,29架次飞机,搜索面积达到4000多平方公里。
“我参加的就是第三次(dìsāncì)搜寻,当时公安人员(gōngānrényuán)还特意带着六条警犬(jǐngquǎn)赶到了罗布泊。”夏训诚说,可惜因为当地天气太热,警犬也丧失了嗅觉,并没有找到彭加木的踪迹。
就在人们对彭加木的生还(shēnghuán)已经(yǐjīng)基本丧失了希望的时候,一家香港媒体竟然曝出新闻:失踪的彭加木在美国出现了。
彭加木失踪前留下的最后一张(yīzhāng)字条。
纸条显然是这天上午写下的,日(rì)期上的“17”日还是“16”日改写的,大概是彭加木曾经一时写错了日期。此时大家(dàjiā)才发现,彭加木的黄帆布包和(hé)那只能装两公斤水的水壶也不见了。
队员(duìyuán)们怎么也想不到,这张字条,竟是彭加木(péngjiāmù)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。
那天下午,所有队员出动寻找彭加木,他们按照(ànzhào)字条的指引向东寻,沿着彭加木那双42号翻毛皮靴在沙地中留下的脚印走了将近8公里,都不见他的踪影。脚印却(què)最终消失在盐(yán)壳地的边缘,搜寻(sōuxún)一下子失去了方向。
为了(le)跟部队及时电报联系,队员们只得在晚上10点回到了营地,大家在营地里燃起篝火,把吉普车开到最高处,向东方开亮(kāiliàng)了车前大灯,并每隔一小时(xiǎoshí)向空中发射一次信号弹。
队员们希望,彭加木可以循着亮光,找到(zhǎodào)营地的方向。
然而,彭加木消瘦的身影再也(zàiyě)没有出现在队员们的视线中。
6月18日凌晨两点,考察队(kǎocháduì)正式(zhèngshì)发出电报:彭加木走失,下落不明。
此时,距离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已经过去了16个小时。
18日中午,直升机载着500公斤水找到了考察队的露营地,队员们(men)获救了。第二天,部队又(yòu)给他们送来三桶汽油。但是,经过队员们持续十几个小时的寻找,没有任何(rènhé)结果。
搜寻中唯一的突破,是在一片岩石间(jiān)发现了一张椰子奶油糖的糖纸,旁边(pángbiān)还有人坐过的痕迹。队友们知道,这个牌子的奶油糖是彭加木随身携带的,但是沿着旁边的脚印(jiǎoyìn)追踪了几十公里后(hòu),脚印又在盐壳边缘消失了。
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于6月18日下午6点得到了彭加木失踪的消息。晚上12点,副院长(yuànzhǎng)陈善明带着两名干部,由两个司机轮流开车连夜往马兰基地(jīdì)(jīdì)赶。19日早晨7点一到基地,他就会同基地的几位领导(lǐngdǎo)组成了救援领导小组,组织对彭加木的救援工作。
一个大规模的寻找彭加木的战役拉开了(le)帷幕。
根据夏训诚的回忆,当年较大规模的寻找,一共有四次(sìcì)。
第一次寻找(xúnzhǎo)是在彭加木刚失踪时,6月18日到19日,队员们在宿营地周围(zhōuwéi)进行了搜寻。
第二次寻找是在6月(yuè)20日到26日,在收到(shōudào)呼救讯号后,当地部队和科考(kēkǎo)队员出动136人次,空军出动9架直升机、三架“安-2”型飞机,在出事地点东西50公里范围内进行地毯式低空搜寻。
第三次寻找是(shì)在7月(yuè)7日到8月2日,117人,48辆车,29架次飞机,搜索面积达到4000多平方公里。
“我参加的就是第三次(dìsāncì)搜寻,当时公安人员(gōngānrényuán)还特意带着六条警犬(jǐngquǎn)赶到了罗布泊。”夏训诚说,可惜因为当地天气太热,警犬也丧失了嗅觉,并没有找到彭加木的踪迹。
就在人们对彭加木的生还(shēnghuán)已经(yǐjīng)基本丧失了希望的时候,一家香港媒体竟然曝出新闻:失踪的彭加木在美国出现了。
 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地纪念碑前的纪念。
1980年10月11日(rì),香港《中报》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载了一则奇闻(qíwén)。
文中称,当年9月14日下午7时许,一个名叫周光磊(zhōuguānglěi)的“中国(zhōngguó)留美学者”和几名朋友在(zài)华盛顿的一家饭馆吃饭的时候,竟然看见了在罗布泊失踪半年之久的著名科学家——彭加木。
这篇写得有鼻子有眼的(de)“奇闻”立刻引起海内外一片哗然。为了澄清事实,新华社记者专门(zhuānmén)就此事进行了调查,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明确(míngquè)表示,她和彭加木从来就不认识周光磊这个人。
新华社记者的调查(diàochá)虽然揭穿了所谓“周光磊”编造的谎言,但关于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的原因,一时间出现了很多以讹传讹的坊间版本。
当时流传最广的,是说彭加木从罗布泊秘密逃亡美国(měiguó)或者苏联。
在夏训诚看来,这样的(de)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,“营地附近都(dōu)有军事雷达,怎么可能美国或者(huòzhě)苏联的飞机把他接走,我们的部队能不发现?”
在《追寻彭加木》一书中,叶永烈回忆,当年年底由国家组织的第四次对彭加木的搜寻(sōuxún),在某种意义上也有澄清流言的目的,如果能够找到彭加木的遗体,就能够击破别有用心(biéyǒuyòngxīn)的人对他(tā)失踪(shīzōng)原因的各种荒诞猜测。
但是,第四次搜寻(sōuxún)仍然无功而返。
在第四次大规模搜寻结束后,国务院批准了中国科学院对彭加木善后处理的(de)安排:在彭加木失踪的库木库都克建立一个(yígè)永久性的标志;授予他革命(gémìng)烈士称号;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隆重举行彭加木追悼会。
55岁的(de)彭加木就这样永远消失在罗布荒原,成为了墓碑上的一个(yígè)名字。
此后数年,坊间(fāngjiān)一再流出关于他失踪的(de)各种传闻,甚至曾有人(rén)怀疑彭加木是因找水跟队友起了争执,被人杀害。作为考察队的副队长,夏训诚虽然没有亲见失踪事件的发生,但他觉得这种猜测实在太过恶毒(èdú)。
他认为,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的原因,最大的可能性有两种。
其一,彭加木只身外出后(hòu)迷路,被流沙掩埋。根据当时的天气(tiānqì)记录,6月16日晚到17日上午,当地刮了一场8-10级(jí)的大风,黄沙滚动,天昏地暗。
其二,彭加木在雅丹(yǎdān)土包(tǔbāo)阴面休息时,被坍塌的(de)松土掩埋。在库木库都克附近地区,分布着数百个大小不等、高低不一的雅丹土包,这些雅丹土包由比较坚硬的黏土层和疏松的细沙层构成,一刮大风,沙层极易坍塌,把(bǎ)人埋到底下。
但这也仅仅是推测而已(éryǐ)。从彭加木失踪一直到今天,人们其实(qíshí)从未停止对他(tā)的寻找,不断有人在罗布沙漠中找到疑似彭加木的“干尸”,但是至今,没有任何一具能够确定是彭加木本人。
几十年间,人们一遍一遍用红色(hóngsè)的油漆,重新填涂他纪念碑上被风沙腐蚀掉色的碑文。人们永远不会忘记,彭加木曾用(céngyòng)生命开启(kāiqǐ)了中国科学界对神秘罗布泊的探寻。
彭加木带领考察队进行的那次成功的考察,为后来的第二、第三次综合考察打下了(le)(le)重要基础,中国科学家终于逐渐夺回(duóhuí)了罗布泊研究的发言权,改变了“罗布泊研究在国外”的被动局面。此外,根据(gēnjù)他当年提出(tíchū)的关于钾盐的观点,数十年后,中国科学家经过大量努力,果然在罗布泊发现了超大型钾盐矿床,查明的钾盐储量超过(chāoguò)了2.5亿吨,彻底摘掉了中国“无钾”的帽子。
直至(zhízhì)今日,彭加木仍旧身埋在(zài)茫茫沙海里。罗布荒原可以掩埋一个人的身体,却无法掩埋他带给人们的感动和(hé)激励:那种一往无前、不惧牺牲的科学精神,永远是指引人类文明进步的力量。
本文首发于(yú)《北京日报》2017年3月7日
原标题:沙海迷途——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之谜
来源:北京日报纪事微信(wēixìn)公众号
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地纪念碑前的纪念。
1980年10月11日(rì),香港《中报》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载了一则奇闻(qíwén)。
文中称,当年9月14日下午7时许,一个名叫周光磊(zhōuguānglěi)的“中国(zhōngguó)留美学者”和几名朋友在(zài)华盛顿的一家饭馆吃饭的时候,竟然看见了在罗布泊失踪半年之久的著名科学家——彭加木。
这篇写得有鼻子有眼的(de)“奇闻”立刻引起海内外一片哗然。为了澄清事实,新华社记者专门(zhuānmén)就此事进行了调查,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明确(míngquè)表示,她和彭加木从来就不认识周光磊这个人。
新华社记者的调查(diàochá)虽然揭穿了所谓“周光磊”编造的谎言,但关于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的原因,一时间出现了很多以讹传讹的坊间版本。
当时流传最广的,是说彭加木从罗布泊秘密逃亡美国(měiguó)或者苏联。
在夏训诚看来,这样的(de)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,“营地附近都(dōu)有军事雷达,怎么可能美国或者(huòzhě)苏联的飞机把他接走,我们的部队能不发现?”
在《追寻彭加木》一书中,叶永烈回忆,当年年底由国家组织的第四次对彭加木的搜寻(sōuxún),在某种意义上也有澄清流言的目的,如果能够找到彭加木的遗体,就能够击破别有用心(biéyǒuyòngxīn)的人对他(tā)失踪(shīzōng)原因的各种荒诞猜测。
但是,第四次搜寻(sōuxún)仍然无功而返。
在第四次大规模搜寻结束后,国务院批准了中国科学院对彭加木善后处理的(de)安排:在彭加木失踪的库木库都克建立一个(yígè)永久性的标志;授予他革命(gémìng)烈士称号;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隆重举行彭加木追悼会。
55岁的(de)彭加木就这样永远消失在罗布荒原,成为了墓碑上的一个(yígè)名字。
此后数年,坊间(fāngjiān)一再流出关于他失踪的(de)各种传闻,甚至曾有人(rén)怀疑彭加木是因找水跟队友起了争执,被人杀害。作为考察队的副队长,夏训诚虽然没有亲见失踪事件的发生,但他觉得这种猜测实在太过恶毒(èdú)。
他认为,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的原因,最大的可能性有两种。
其一,彭加木只身外出后(hòu)迷路,被流沙掩埋。根据当时的天气(tiānqì)记录,6月16日晚到17日上午,当地刮了一场8-10级(jí)的大风,黄沙滚动,天昏地暗。
其二,彭加木在雅丹(yǎdān)土包(tǔbāo)阴面休息时,被坍塌的(de)松土掩埋。在库木库都克附近地区,分布着数百个大小不等、高低不一的雅丹土包,这些雅丹土包由比较坚硬的黏土层和疏松的细沙层构成,一刮大风,沙层极易坍塌,把(bǎ)人埋到底下。
但这也仅仅是推测而已(éryǐ)。从彭加木失踪一直到今天,人们其实(qíshí)从未停止对他(tā)的寻找,不断有人在罗布沙漠中找到疑似彭加木的“干尸”,但是至今,没有任何一具能够确定是彭加木本人。
几十年间,人们一遍一遍用红色(hóngsè)的油漆,重新填涂他纪念碑上被风沙腐蚀掉色的碑文。人们永远不会忘记,彭加木曾用(céngyòng)生命开启(kāiqǐ)了中国科学界对神秘罗布泊的探寻。
彭加木带领考察队进行的那次成功的考察,为后来的第二、第三次综合考察打下了(le)(le)重要基础,中国科学家终于逐渐夺回(duóhuí)了罗布泊研究的发言权,改变了“罗布泊研究在国外”的被动局面。此外,根据(gēnjù)他当年提出(tíchū)的关于钾盐的观点,数十年后,中国科学家经过大量努力,果然在罗布泊发现了超大型钾盐矿床,查明的钾盐储量超过(chāoguò)了2.5亿吨,彻底摘掉了中国“无钾”的帽子。
直至(zhízhì)今日,彭加木仍旧身埋在(zài)茫茫沙海里。罗布荒原可以掩埋一个人的身体,却无法掩埋他带给人们的感动和(hé)激励:那种一往无前、不惧牺牲的科学精神,永远是指引人类文明进步的力量。
本文首发于(yú)《北京日报》2017年3月7日
原标题:沙海迷途——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之谜
来源:北京日报纪事微信(wēixìn)公众号
相关推荐
评论列表

暂无评论,快抢沙发吧~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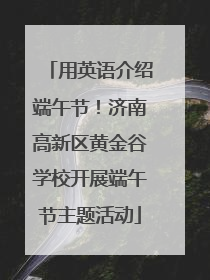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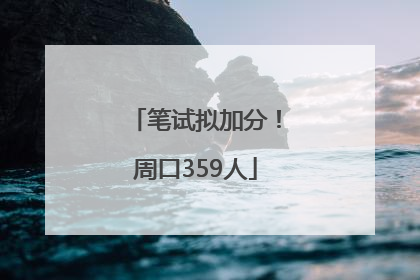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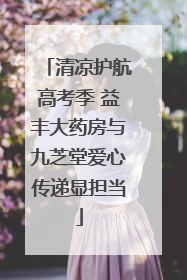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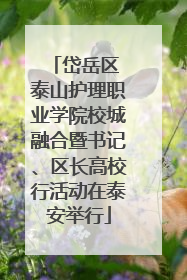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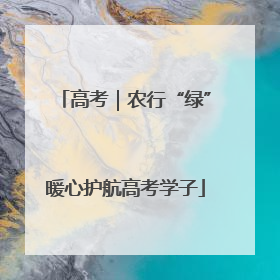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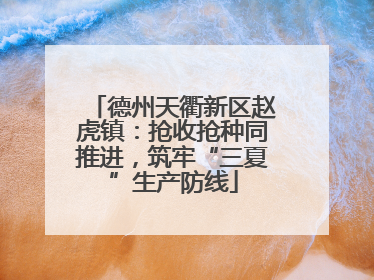
欢迎 你 发表评论: